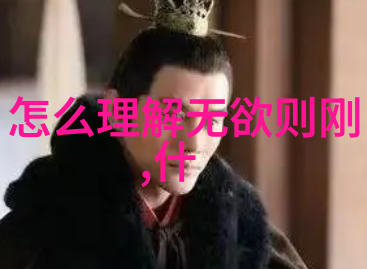道德经原版全篇庄子马蹄 仁义枷锁何曾拘束自然本性
张永祥《马蹄》开篇即言马之本性:食草饮水,奔腾欢悦,活得悠然自得,颇具风骨。伯乐一来,从此汩没性灵。庄子用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动词,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幅真实到近乎残酷的伯乐治马画面:“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 之、渴 之、驰 之、骤 之、整 之、齐 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荚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儿身上遍是伤痕,死者过半,受尽苦难与折磨的幸存者,也只能在鞭子下和车套中苟延残喘,度过丧失尊严的余生。而这一切,只为了伯乐的一句“我善治马”!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不曾考虑过其他生物的心理感受,更不曾想过它们如何被迫改变自己的本能,以适应人类的需要。

人作为万物灵长,却常将万物视为自己而生,用着“万物为我所用”的态度。即使善于识人的伯乐,也不能适合动物天性的使用,而是强行施加暴力,以便让它们服从于人类,并付出生命代价。这是多么残忍!使动物丧失其自然本性,在鞭子的驱策下和车轮之间挣扎求生的过程中,它们已经失去了自由奔放的天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一匹最快捷或最英勇的大型野兽,也会被训练成遵循人类意志而忘却了它原本要追逐自由生活的情感。
东晋末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地球,那里没有纷争,没有差别,每个人都对他人充满友爱和同情;鸟巢里的小鸟也不害怕人们爬上树来窥探,“彼民有常性”,他们不知其所以生,所以得,所以安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正是庄子的理想社会——至德时期。在那个时代,没有欲望,没有贪婪,无需技巧去驯养动物,因为百姓无知又无欲,他们如同生活在远古美好宁静的地方。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则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一些知识分子渴望实现这样一个平静安宁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共存的情况,但他们发现这种愿望似乎总是在遥不可及。面对荒唐世俗道德约束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我们应当反思并试图超越这些限制,让我们的行为更加接近那份纯真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点,那么每个人都能像庄子的神人一样,被尘垢秕糠所覆盖但仍保持清净,如同陶渊明中的桃花源居民那样享受生命中的简单快乐。但对于那些仍旧沉浸于文明规范下的现代人来说,这样的境界似乎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事迹,只剩下回忆和梦想了。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野蛮人所以不是恶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这句话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社会虽然拥有丰富知识与法律法规,但还是无法避免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大自然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当我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外部世界,还包括我们内心深处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善”、“恶”、“美”的问题时,我们可能就更接近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步伐。那时候,或许我们的行为才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将“仁义礼”的名声挂起口头,却忽略掉它们背后的意义,从而导致道德日废,对个体精神自由造成进一步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