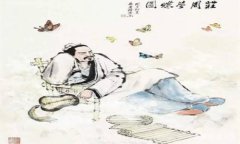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也就是皇权与神权的关系。我国自远古夏商周三代起直至清末为止一直被君主统治着,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使、伦理与宗教三者构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作者从这个观点出发,系统地、历史地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外来宗教与皇权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天帝崇拜、三统的说教和谶语符命等等无不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和国运昌盛或转移的神话;道教在魏晋以后开始与统治阶级相妥协,臣服于皇权,道教自身的内容也相应地有了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依附于统治阶级,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南北朝开始,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扶持、奖掖和利用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进行严密的防范和管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唐宋时期统治者一般采取怀柔、保护和扶持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唐以后传入的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天主教等一直采取宽容、保护、限制和同化的政策,但这都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因之,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权杖与皇冠”相斗争的事件。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因而佛道的信仰从来未占据过统治地位。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的宗教观念从一开始就把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的勤苦耕耘置于同等的重要地位,把天或神的意志和人的意见放在同一地位上。周代以后儒家主张以德治天下,敬天而不信天。“敬鬼神而远之”的“神道设教”的思想,在中国一直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君权神授,受命于天,自居天子之位,王权高于神权。因此既利用宗教教化的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华夏民族在周代就形成了一套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性社会制度和祖先崇拜,数千年来渗透到汉族的每个家庭之中,成为牢固的民间习俗。另外儒家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的伦理观念,使汉族形成了务实的特点,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宗的面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就不信。为了求得庇佑,不论是儒释道,还是鬼神上帝,或是菩萨圣母都可以信仰。由于宗法社会制度和儒家重视道德伦理思想同崇拜超人力量的宗教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正统儒家文化必然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起抑制作用。
这一切说明宗教在中国有它自己的特殊形态,与国外的宗教流行和发展大不一样。基于这个观点,我们讨论一下中国宗教中的政教关系的情况。
关于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也就是皇权与神权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古代的埃及、波斯等东方国家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但和西方相比是不同的。在西欧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5~17世纪),教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因此有着普世的绝对神权,在那里教权、君权和主权是可以区分的,教权在教会,教权可以超越君权和主权,甚至具有册封或加冕国王之权。因之在西欧中世纪时期曾多次发生“权杖与皇冠”的斗争事件,这在中国是罕见的。
中国在古代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的国家,自远古的夏商周三代起直至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都被属于一姓的君主所统治,君主通过他的各级官吏控制和管理着臣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以君权至上为核心和以宗族宗教伦理为本位的宗法制度,规定了它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反过来又制约着宗族伦理体制的发展,因此,在国家生活中、伦理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三者构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
中国古代出现过种种官方神学,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为宗法制度和制度服务的。例如,在古代传统宗教中,常常宣传的天帝、五帝(黄帝居中,其余四帝属于四个方位)的崇拜;五德终始(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的组合与转换,意味着国运的变化);三统(夏商周是本于天的三正统)的说教;谶语符命的迷信;灾异谴责的预言等,无不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和国运昌盛或转移的神话。另外,作为皇室总代表的天子或皇帝还独揽了祭祀天神、皇族先祖及对国家有贡献的英雄人物的权利。例如,表示“天授祖予”的祭天地、祀上帝百神、封泰山、禅梁父等。在这些统治者看来,宗庙是国家的象征,宗庙被毁,也就意味着一姓王权的覆灭。
君权神授的观念最早见于夏代。夏禹在征伐有扈氏(部落)时称:“天用剿绝其命”,而自己是“共行天下之罚也。”(《墨子》引“禹誓”)。这个观念在商代得到了系统的阐述,赋于了新的内容。作为官方文学《尚书》的《周诰》十二篇中提到“天命”或“上帝之命”就有73 处。又如《诗经》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
颇堪注意的是,周代对天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新天命的思想,认为王者必须“明德”、“崇德”、“敬德”、“同德”才能维系自己的统治权力,这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神学的开端。从此中国历代帝王都以“德政”(以德治天下)为标榜,作为他们的理想。天命思想在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西汉初年,儒家今文学家董仲舒(前199~前104)树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使儒学系统走上了神学的道路。他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天用符瑞或灾害来指导帝王的行动,所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他鼓吹“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说封建道德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在具体措施上还是应该像“琴瑟改弦”一样有所变化。另外,他还鼓吹“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从此封建统治的四种权利政权、神权、族权、夫权长期束缚中国人的行动。由是可以看出,儒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它的教化作用也起着宗教的社会功能。
道教是我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最早在民间活动。汉末的太平道曾组织黄巾农民大起义,他们提出了“太平世道”的理想。这种理想一直鼓舞着中国的农民,但在封建社会中又是无法实现的。魏晋以后,道教在统治阶级的武力威胁和利禄的引诱下,开始与统治阶级妥协,臣服于皇权之下,道教自身的内容也相应地有了变化,不少道士把民间道教引向了神仙道教,或者改造成适合于贵族需要的道教,从而出现了具有全国性规模的天师道等等。晋代著名道士葛洪坚决维护君权及纲常名教。他说“君,天也父也。”(《良规》)“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微旨》)南朝的陶弘景积极为萧衍纂夺齐政权制造,以后成了梁朝皇帝的谋士。《南史·陶弘景传》云:“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北魏寇谦之改革了旧天师道,提倡“以礼度为首”,制订了《太上经戒》,其中十戒里明确规定有“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国家”等内容。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有时道教居先,不少道士积极参与活动。唐太宗在得天下之后所发布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可见唐初道教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道教经历了南宋金元的宗派分化以后,到明朝中叶以前,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发展到了极为贵盛的地步。不少道被国家委以重要的官职,深入宫廷,参与朝政,位极人臣,声势显赫,为历代所罕见。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教规和组织,但在我国历史各个阶段中,佛教教团的势力一直是从属于朝廷的,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管理,甚至成为政府的一个组成或派生的部分。佛教最初是通过国家的渠道传入中国的。公元一世纪以后,汉明帝首先派遣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问道佛法,从此佛教开始在我国传播。初传时依附于黄老之学和神仙之术,传播的范围只在上层社会。后汉桓帝是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他信奉的目的是为了求神庇佑,挽救垂死的王朝。魏晋时期,佛教依附于玄学,开始中国化的过程,得到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推行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影响。南朝宋、齐、梁、陈诸帝和北朝除“二武”(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以外的统治者们都热衷于佛教的信仰和事业。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同声宣传印度传来的“转轮王”和“法王”的理想,自翊是“法主”、“佛法寄嘱人王”。东晋时曾开展一场“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重臣桓玄想要僧人礼敬王者,但遭到了以慧远为首的僧侣的强烈反对。慧远举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如果沙门成就了功德,达到了成佛的目标,也就是“助王化于治道”,因此可以不必向王者屈膝行礼,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皇权与教权的斗争,慧远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是巩固了皇权。东晋另一个高僧道安也公开宣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北魏僧统法果说:“能鸿(宏——引者)道者人主也,我非是拜天,乃是礼佛也。”他甚至把皇帝称为“当今如来”。宋文帝宣称:佛教是“行善、去恶、息刑的‘神道助教。’”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教化,则我坐致太平。”这又可以看出,当时佛教所起的社会作用。在统治阶级的支持、扶植下,很多王朝便大事度僧、造寺、铸像、治经,并互相攀比,糜费了大量的国库资金。宋文帝为了“供养三宝”,竟耗去国家储备的三分之一。南北朝的统治者们一方面大力扶持、奖掖和利用佛教,另一方面也对佛教进行严密的防范和管制,自南北朝开始,政府就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职,对佛教事务进行监督和管理,当佛教在、经济方面一旦和朝廷的利益发生龃龉或矛盾时,朝廷便毫不吝惜的加以限制、取缔,甚至进行。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四次被佛称为“法难”的,其中二次就在这段时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所以要采取取缔佛教的行动,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佛教对他们的政权将可能产生威胁,皇权受到了挑战。当然因素也有一些,但远不如这个原因重要。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现象,在社会中最终都会在上有所反映。
隋唐是佛教鼎盛阶段,佛教的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教权在皇权之下。隋文帝在历史上以佞佛而著称。他从小生养在尼庵中,受佛教的薰陶甚深。登基后曾宣称:“佛以,付嘱国王,联是人尊,受佛咐嘱。”明显的将“君权神授”的观念强加于天下。又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他在造寺、治经、铸像、度僧方面做了大量的活动。另一位隋场帝也自称是“菩萨戒、皇帝总持”。他在京城或出外巡行时,总要带上一批僧、尼、道士、道姑,谓之“四道场”,尽情欢乐,“酒酣肴乱,靡所不至,以为是常。”(《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佛门的清净和自律的戒规,在这位的眼里已经荡然无存,无法可依,皇权可以随意打破佛门的传统教权。再看看唐代,22个皇帝中除武宗李炎外,个个都信佛。武则天为了想当大周皇帝,参与了制造《大云经》的神话。道宣概括唐朝佛教的情况说:“皇唐御历,道务是崇,义学之明,方为弘远。”(《续僧传》卷一五)而北宋除徽宗崇道外,其余七帝也是信佛者,对佛教采取庇护、利用的政策。宋太宗自称是佛子再世(“朕曩世尝亲佛座”),“素仰释教”,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于,……联于此道,微究宗旨。”(《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三)“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宋会要辑稿·道释一》)至于偏安临安的南宋,更加依赖、庇护佛教,以维护他们的摇摇欲坠的王朝。在这个佛教臻于鼎盛并延伸的时期,佛教与国家的关系大致有如下的特点:
(1)在隋唐两宋时期,统治者奉行的是以儒学为本的方针,他们清楚地懂得宗教神学必须服从、经济、军事的目的,儒学的伦理纲常是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儒教大一统的礼乐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也。”(《慎所好》)但是他们也采取兼容并蓄,多教并行的方针,充分发挥各教的有利作用,使之为国家政权服务。纵观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社会以及统治者的主观信仰等等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佛教的态度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是采取扶助、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当时“三教融合”,“三教无阙”,“会三归一”已是时代的潮流,在统治者看来,佛教的伦理可以弥补儒家伦理的功能,有益于皇家的教化作用。
(2)唐代统治者为了扶持佛教,不惜动用国库的钱帑,不顾民生疾苦,建造了大量的寺院、塔幢、佛像等等,度僧无数。另外,大力支持治经、译经事业,建立国家译场,招引礼遇名僧贤士,进行大规模译经的活动。例如,唐太宗为玄奘在长安建立了规模宏大、制度严密的译场,玄奘得以译出了佛经75部、1335卷,约占唐代译经总量的二分之一。宋太宗为印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人在开封设置了译经院,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到仁宗景佑二年(1035)的54年中,共译出了梵本1428夹,564卷。
(3)国家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监督和管理,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僧职系列和行政管理制度。北魏管理佛教等事务的机构是设在中央的昭玄寺,长官为僧人。唐代管理僧尼的是尚书省礼部的祠部,长官均由俗人任职,但需经祠部批准任命,这使佛教管理成了世俗行政的一部分。另外,为了控制僧侣人数,唐宋沿袭旧制采用度牒制度,还建立了专门的僧道户籍,甚至容许僧伽在一定范围内有司法审理的权利。再次,国家通过唐初的均田制和以后颁行的寺观常住田的标准,直接控制寺院的经济,借以遏制僧侣地主的兼并和寺院经济的膨胀,但事实证明,这种经济干预只起到了部分作用。
(4)如上所述,唐宋时期对佛教的政策,凡有利于皇权的就扶植、利用,不利的则毫不犹豫地进行干涉、打击,甚至尽行消灭。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的禁佛事件或“法难”,唐宋之际出现的唐武宗和周世宗的禁佛事件,都是统治阶级对佛教发展过滥所采取的打击行动。唐武宗“会昌二年”的“会昌法难”,共拆寺庙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小寺庙)4万余所,收膏腴良田数千万顷。这次禁佛事件虽然起因于道教,武宗溺爱道教,因此佛道发生了矛盾,道教假统治者之手来打击佛教,但在这一事实后面还可以看到有着深刻的背景,正如武宗废佛敕所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可见“土木之功”和“金宝之饰”的问题才是禁佛的主要原因之一。后周武宗禁佛发生于显德二年(955),共废寺3336所,废佛的主要原因还是僧尼管理功能渐驰,寺僧浮滥,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赋税与兵役。
===首页与分页与分页之间分隔符===
元明以后,中国佛教已进入了衰颓时期,这时佛教的特点是步趋前人,陈陈推因。统治者们继续鼓吹以儒教性理学为中心等等的德治思想,但对佛教仍采取拉拢、奖掖的政策。元世祖忽必烈称:“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佛祖统纪》卷四八)《元史》在概括元朝的佛教情况时曾说:“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元史·释老传》)元朝以前中国佛教中常有帝王敕封的国师,未见有帝师。元世祖于1260年即位后就封藏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帝师,以后相袭成制,历十二世。帝师位处“皇天之下,一人之上”,“所统僧人,并土番军民等事”。《元史·释老传》在陈述元朝设立帝师制度的缘由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乃得西域,世祖从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总其于内外者,师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从这里可以看出,元朝设立帝师制度完全出于需要,一方面借以拉拢、控制藏蒙民族;另一方面要加强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种帝师制度,清朝、沿袭之,但赋与了新的形式。14世纪宗喀巴改革黄教在藏蒙地区占有统治地位后,黄教的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转世系统,包括和班禅的名号都是由皇帝册封的。例如,1653年清顺治帝颁赐金印、金册敕封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康熙五十二年(1731)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确定了达喇和班禅必须由朝廷册封的制度,同时,历代皇朝中央政府都拥有册封或褫革这种名号的绝对权威。清末发生褫革第十三世达喇名号就是证明。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教权和政权的结合在是最典型的,显赫的神权是为世俗的皇权服务的,而神权的确立,最后还是靠皇权的赐与。
伊斯兰教是外来的宗教之一。唐高宗时(651)由阿拉伯传入中国,迄明末清初,作为伊斯兰的主体才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伊斯兰教是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宗教,在阿拉伯世界一直就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但其传入中国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伊斯兰教的教权一直从属于王权,并始终受到了朝廷的监护和管理。中国历朝统治者对伊斯兰教一般采取怀柔、保护和扶持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中唐以后,由于大食国曾协助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大批伊斯兰定居在中国,因此,朝廷对他们采取了极为宽容、友好的态度。宋朝时,由于海上贸易十分兴盛,朝廷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取自阿拉伯商人的市舶,因此穆斯林受到了优渥礼待,政府在广州等地设蕃坊,置蕃长,穆斯林则由蕃长自行管理,类似现代的“治外法权”,另外也辖有一定的司法权。如《宋史》所云:“夷人有犯,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宋史·张蛊传》)至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已经传遍中国的新疆地区,成为当地人民的全民信仰的宗教。元朝回回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和南人,不少穆斯林在朝廷任要职,直接参与、军事的活动。元时中央设置了“回回国子监”、“回回司天监”、“广惠司”(负责管理回医)、“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回回掌教哈的司”(管理司法事务)等,分别管理穆斯林的教务、教育、历法、医药、司法、军械等事务。
明朝一仍其旧。明太祖在取得穆斯林军人的帮助夺得政权后,一直优渥重用穆斯林官吏。他曾作《圣教百字赞》(也有人认为是伪作),赞扬伊斯兰教。与此同时,朝廷准许外族人与回族穆斯林通婚,以此增加穆斯林中汉人的成分,这是一种对回族或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实行同化的政策。明末清初,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出现了把伊斯兰教经院哲学与儒学相融合的,穆斯林的神学家们把穆圣比作孔圣,将伊斯兰教的“天道五功”(念功、礼拜、戒斋、天课、朝觐)和儒学的人伦五典相比似,以此推进穆斯林的中国化进程。清朝实行以歧视、压迫为主,怀柔为辅的宗教政策,致使酿成多次回民起义。伊斯兰教传入西北地区后,在中央和地区政府的管辖下,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和教坊制度,使宗教的管理纳入了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以内。门宦是宗教领袖的豪门世家,门宦制度是教主兼地主的政教合一的制度。门宦的教主辖有众多的教坊,教坊的教长直接由教主委任,这种制度虽然在教内实行政教一体的统一管理,但门宦的教主仍由政府任命,教权最终还是由世俗政权或皇权所决定的。
在唐宋元明时期,还有景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印度教、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相继传入中国。朝廷为了睦邻、通商、军事等需要,同时为了满足来华使节、商人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要求,允许这些宗教在中国设寺、传教、翻译经典,对他们采取了宽容、保护、限制和同化的政策。
景教——教的一支于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内地。这个教派受到自唐太宗至德宗六代皇帝的庇护。高宗封景教僧人阿罗本为镇国大主教,不少教士在朝廷和军队中担任要职。当时传播的情况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景教在唐代已经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但是这个教派在中国还没有打下深入的基础,于唐武宗毁佛时遭到废止。景教在中国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同样受到皇帝的监督。景教僧人在携入大批景经来中国时,首先要将它们献给皇帝,在皇帝“问道禁闱”,“详其教旨”,判其能“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才“深知正真,特令传授”。外来的宗教在传入中国时,首先要受到官方的研究和检查,然后才准许流行,这表明至少在唐代就已有之,说明唐朝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对外来宗教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措施。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外来的宗教文化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态度,允许各种宗教的传入,其实它还是有限度的,而且还是有选择性的。在唐朝之前,历史上虽然也有过统治阶级出面干涉外来的宗教,如魏太武帝、周武帝所发动的排佛事件,曾经发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这些都是在外来的宗教已经传入以后而发生的,并不是在初传之始就采取的“防范措施”,与唐代执行的对外来的宗教管理政策有着显著的区别。正是景教被官方所认识,才有后来景净译经不得力,被朝廷指出:“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的区别。继景教之后于中国元代流传的教是也里可温(意谓“信奉福音者”)教,这个教派在中国沿海地区和新疆边陲有相当的影响。元朝廷中也有人信奉。元代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崇福司(后改为崇福院)加以管理。元朝被推翻后,也里可温在汉地也随之衰亡。
明末,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传教士们为了适应中国社会情况,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把教神学和中国儒学揉和在一起而加以宣传。他们结交权贵,礼待士大夫,终于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在北京和地区找到了立足之处。利马窦提倡“三父合一”(天主、国君、家父)、“君权至上”的原则。他在《天主实义》开篇中说:“天庸治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主谓也。五伦甲乎君臣,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明此行于此。”天主教传教士虽主张“君权至尊”的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只要触犯了皇帝的尊严和权益,也就受到斥责或驱逐。例如汤若望在修订明朝历法时,使用了“依西洋新法”,引起“历狱”。在皇帝看来,这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正朔是王朝的标帜,如果更换了正朔,也就意味着国家朝代的衰替。
摩尼教(明教)大约在6~7世纪传入中国汉地,不久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地区。763年正式传入漠北回纥,被尊为国教。《国史补》载:回纥国主“常与摩尼议政”,回纥在与唐朝交往中摩尼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外交角色。五代北宋时,摩尼教常常被农民利用为组织起义的旗帜,嗣后,该教又与民间秘密宗教相混合,变成了皇权的障碍,故受到严厉的打击。
琐罗亚斯德教大概与摩尼教同时传入中国。它传入后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者的重视。不少在这些王朝中担任要职,直接参与政事和宫闱的斗争,从北魏直至唐时,在国家政府机构中一直设有管理祆教的祀官——萨宝府官。该教在唐武宗灭佛时也遭到了毁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宗教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几十年来宗教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宗教是可以适应社会主义国情的。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条件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过去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走过来的,过去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存,宗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在世界上,宗教仍然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要与外界交往,也离不开宗教的交流。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宗教仍然会保存下来,作为一种信仰,仍然会拥有一部分信众。从国家看,政府要认真制订、贯彻执行宗教信仰的政策,真正地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上和政策上保证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从宗教方面看,要求宗教在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这并不要求宗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党政府、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时要发扬宗教教义教规、宗教伦理道德、宗教文化艺术、宗教对外交往等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从宗教概念不同层次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还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思想道德建设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宗教中的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很多宗教中某些普遍意义的理论原则、道德箴言、行为准则和辩证的思想方法是与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与实践相契合的。例如,佛教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说,中观、八不的辩证法因素,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持法等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提倡“一种思想、三个传统”。一种思想即“人间佛教”,其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清净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乐有情,庄严国土。三个传统是: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佛教的友好交往,这些都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指出了方向。又如伊斯兰教的圣训中提到“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强调爱国是伊斯兰教信仰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这也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相契合的。
(2)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宗教文化是其中较为重要和突出的部分。这是中国各族宗辛勤艰苦劳动的精神产品,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传统的宗教文化不仅表现在哲学、逻辑、文学艺术、天文历数、医药气功等方面,也呈现在灿烂多姿、蔚为壮观的建筑、文物、器皿、古迹和浩如烟海的经藏之中。例如,中国的敦煌石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宝库之一。现有洞窟700余个,彩塑2000余身,壁画5万平方米,仅藏经洞内就装满了4万余件宗教文物。如龙门、云岗、大足等地的石刻,赵城的金藏等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一页。道为寻求“道法自然”,在探索方术中,客观上对中国的医学、化学和天文学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参同契》是公认的炼丹史上最古的著作。《真元妙道要略》则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实验。总之,这些宗教文化的精华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借鉴或汲取丰富的养料。
(3)由同一信仰构成的社会实体包括着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的信教群众。这部分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是有神论者,但在上是爱国的,拥护政府和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不管在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还是在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以及维护社会安定,加强民族团结,保卫世界和平,改善人类生活环境,促进祖国统一,发展对外友好等方面都有他们的功劳。他们为祖国,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当代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在主流上是共同发展的趋势,宗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虽然中国宗教曾经有过一段弯路,但是通过政府和宗之间的相互努力合作,正在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宗教也会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过,在任何国家,宗教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规,先有国才有教,否则就无从谈起发展。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引自共识网)
(责任编辑:张宗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