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
1957年,站在领奖台上44岁的加缪,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获奖者之一。
他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文学”的代表人物,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被称为“年轻一代的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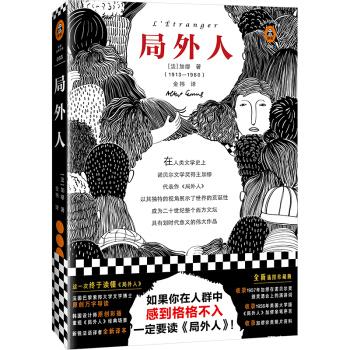
在加缪的所有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中,“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他的成名作《局外人》就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荒诞”的人物——黙尔索。
黙尔索是一个小职员,“我不知道”“毫无意义”这两句话被他挂在嘴边,母亲的葬礼上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面对女朋友提及的婚姻,他回答“我怎么都行”,和劣迹斑斑的邻居交朋友也是无所谓,最后因为“正当防卫”杀人而被捕入狱,而法官判他死刑的理由就是:这个冷漠的人“怀着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荒诞的人物演绎的荒诞故事足以引起任何读者的深思
。
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不在他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
“陪审团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关系,还在电影院看喜剧,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
这就是法官判决黙尔索死刑的理由,母亲去世后,他没有痛哭流涕、悲痛欲绝,所以违背了作为一个“正常人”该遵循的礼教,破坏了正常的规则体系,不遵守游戏规则,因此必须被消灭。
随着社会的发展,礼教从开始的束缚人们粗野行为,演变为机械、虚伪的流程,不再是真情的流露,而是情感的桎梏。

魏晋时期的名士,在逐渐认清当时利用统治者儒家的学说掩饰自己的虚伪后,就开始挑战那些束缚人的教条和规矩,寻找本真的自我。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孝子,他特别讨厌所谓的“礼法伪君子”的惺惺作态,母亲去世的时候,照样吃肉喝酒,这时就有人给皇帝打小报告了:您以孝治天下,阮籍居然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有伤风化,应该把他这种人流放到海外!
所幸,小皇帝爱才,此事不了了之。
阮籍不尊礼法,差点惹来杀身之祸,而黙尔索不尊礼法,真的要被砍头。在道德礼教的框架之下,你必须注重外在的形式,表面的功夫,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都必须机械走完规定的流程,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人”。

鲁迅先生说:“吃人的礼教”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礼教成为官方道德的标准,就变成了杀人的工具。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伤痛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鯈(tiáo)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吾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吾,吾知之濠上也。
——《庄子·秋水》
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以为”,就像一位名人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人们往往只看到表面就妄作决定,超出礼教道德范围的就是离经叛道,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要求流放阮籍的官员,只看到阮籍喝酒吃肉,没有看到阮籍丧母以后因为过度悲伤而瘦骨嶙嶙。
而判黙尔索死刑的法官只看到法庭上的黙尔索冷漠的外表,只听说黙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去游泳、找女人,他没看到黙尔索对母亲也有真情的一面。
听说母亲去世,黙尔索请假、借葬礼上穿的衣服,坐几个小时的长途车,然后走两公里的路到达养老院。
“我想立刻见到母亲,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
黙尔索只得按照门房、院长的指示去做,心力交瘁的他漠然机械地走完为母亲送葬的流程(这就是他被判死刑的理由)。
葬礼后回到家里,黙尔索睡觉、游泳、和女友戏耍,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何尝不是想着去世的母亲?
“妈妈在世的时候,这套房子还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太大了,我不得不把饭厅的桌子搬到卧室来。”
母亲的影子无所不在,母亲走了心空了,所以房子也空了。

就像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我不流泪并不代表我不伤心,我伤心不一定表现在脸上。
有多少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把礼节和面子做的滴水不漏,背后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庄子的“超然物外”与存在主义的“荒诞”
庄子的妻子去世,惠子去看他,没有想象中的而悲痛,庄子坐在地上,敲着盆子在唱歌。
惠子责怪他:相伴几十年的而夫妻去世,你不伤心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这么高兴?
庄子回答说:妻子死了,我这么会不难过,只是人最初是乜有生命的,也没有形体,在若有若无恍恍惚惚将,那最原始的的东西经过变化而产生形体,又经过变化而产生生命,这种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样运行不止,现在她静静的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却还要哭哭啼啼,这太不通达了……

庄子认为,既然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那么人就可以坦然接受生死。
道家讲究“超然物外”,因为对万物自然本性有理解,他也就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在世俗中,他就是一个“局外人”。
黙尔索也一直是“局外人”的角色,他接受妈妈的死亡,认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所以葬礼上的他没有眼泪;在审判自己的法庭上,他更是一个妥妥的“局外人”,证人的叙述、法官的臆断、律师辩护,都与他有关,但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黙尔索在考虑要不要上诉时,盘算胜诉的可能,幡然悔悟:“三十岁死或者七十岁死并没有什么区别……人既是要死的,那么,怎么个死法、什么时间死这些都不重要……”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这样说:由于世界对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报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对事物的无动于衷”和庄子们的“坦然接受生死”是一样的道理,都是看破人生的荒诞之后,才拥有的安宁。
“
超然物外”也好,“荒诞”也罢,表达的都是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对人类良知道德的观察与反思。
黙尔索(加缪)与庄子,注定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异类”,是寻找怎么走入“局内”的“局外人”。
参考资料:《中国哲学简史》 《世说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