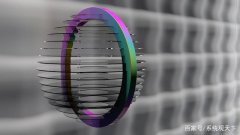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在中国社会中不占主流,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入世的哲学,强调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一种积极为国为民实现个人理想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隐士文化格格不入。

而中国文化是多元构成的文化,除了积极进取的儒家,还有倡导清静无为的道家,倡导超越俗世放下执着的佛家。而道家与佛家,似乎天生与隐士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隐士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
从知识分子隐居的目的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可奈何走向隐居之路的,一类是心甘情愿藏身林泉烟海的,或者可以说,一类是真隐士,一类是假隐士。
真隐士看透了世事的荒凉,以决绝的姿态告别红尘,走向林泉走向内心的宁静;假隐士则是将隐居作为求名求官的以退为进的手段,实现走出林泉走向庙堂的目的。唐朝时期包括李白在内的大部分隐士都是如此,他们选在距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假装隐居,眼睛则望着长安城的一举一动,准备随时靠着终南捷径走向长安。
在隐士的发展史上,隐士们发明了很多种隐居的方式,这些方式影响了隐士的心态,考察这些隐居的方式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隐士文化和他们的心态。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事实上他也是儒家隐士观念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到六十多岁还希望到楚国做官,为了显示决心,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看样子是不可能隐居的。
但儒家思想又有现实理性的因素,这种思想孔子叫“中庸”,孟子叫“权变”,这意味着儒家以有利合适为目的,不会僵化死守一种思想,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所以儒家子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也会想到去做隐士,连孔子也是如此。
孔子一生很努力,但结果不甚如意。他遇见过很多避世的隐士,他虽然表面上说“鸟兽不可以同群”,但有时候也有隐居避世的思想,他曾经告诉说“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但孔子又给隐居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道之不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孟子所讲的“仁政”与“王道”理想,当天下昏暗一团乱麻无法收拾的时候,才可以躲起来去隐居。

这种思想被孟子总结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数千年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信条,居庙堂之上则为国为民,处江湖之远则完善自我,这也是中国隐士文化最根本的基调。
孔子的“道隐”,说到底颇有一些不情不愿的样子。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社会,居庙堂之上是首要追求,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处江湖之远。大部分隐士都是在人生遇到挫折或难解的心结之时,才回到大自然之中去。
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屈尊高贵的灵魂;孟浩然几次科举考试无功而返灰心灰意冷才回归襄阳;李白假装隐居很显然是走“终南捷径”;唐伯虎是上了科举考试的黑榜,再无机会的情况下才营造桃花庵开始过神仙生活的。总之,他们的隐居是无奈的,而真正把隐居当成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不掺杂功利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纯正的隐士,这个人是庄子。

庄子当时的地位与名声其实比孔子大得多,他隐居乡间穷困潦倒,穿草鞋破衣服问河间侯借粮食,而魏国和楚国人都要来请他去做大官,但庄子傲视王侯粪土富贵,在他看来,与其风光地在朝堂上做死去的祭品,还不如做污泥中自由自在的乌龟。他从一开始就将隐居当成一种纯粹的审美生活,这与庄子的审美和哲学理念有关。
庄子的终极理想是实现“逍遥”境界,而“逍遥”的前提是“无所待”。人不能被红尘的种种俗事牵绊,如功名利禄无和尽的。但人又不能完全脱离物,所以,庄子天才地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论,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驾驭物,但不能成为物的奴隶。
所以在庄子看来,在哪里隐居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保持心灵的逍遥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的隐居其实是“心隐”,无论你处于何时何地,只要你的心是超脱的,灵魂就是自由的。隐居不一定要躲到四野苍茫的地方,只要心能逍遥自在,这就是隐居的大境界。
魏晋时代的大隐士陶渊明深得庄子思想三昧,他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他还是躲到了南山下偷偷看菊花——毕竟心无挂碍自在逍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