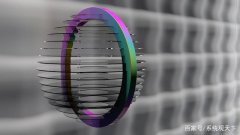微信搜索“中式大美生活”
我们曾以为,自由是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后来我们发现,这不可能。
在庄子看来,自由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感受与追求,是一种主客观之间无任何对立与冲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无任何牵系与负累的超然心境。
这是一种极高极难的境界,但却是“有可能”的。
庄子眼中的“自由”分两种:
绝对的自由。
它无需凭借任何外力,是“无待”的,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相对的自由。
便是“道遥游”:“逍”是消释而无执滞,“遥”是随顺而无抵触,“游”是无所拘碍的自由自得状态。
就像《逍遥游》中的大鹏与列子,“九万里风鹏正举”,他们固然任情适意,但仍然“有所待”——凭借六月飓风所掀起的波涛的托浮,才能背负青天,毫无阻碍地飞往南冥。
若条件一变,这种自由便随之消失。
人类社会,多数时代、多数人,要么汲汲营营,成为他人的工具;要么沦为自己情志、的奴隶;要么变作种种身外之物的殉葬品,完全忘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如今又有何不同呢?尤其当我们受环境影响,不得不将身体局限在一个小空间的时候,内心涌现的那些对现实的惊恐、对未来的忧惧,比忙碌时更加纷乱。

绝对的自由不强求,相对的自由如何获得?
在古代,有人选择做隐士,但是“隐身容易隐心难”,即使找了一个远离尘嚣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也不一定能使灵魂感到安宁。
为此,他们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从那些无利害冲突、超出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这对于当前大多数普通人,自然是不可取的。而庄子,是这样做的:
他无意于像儒家那样积极入世,也不主张遁迹山林,逃避社会,而是采取“顺世”、“游世”、“间世”的态度。
身处红尘,而超然物外。既不完全逃离,又能拉开距离,这就是“逍遥游”的理想境界。
庄子曾说,人如果能够游心自适,哪里有不悠游自得的呢?人如果不能游心自适,哪里有悠游自得的呢?
内心生活充实了,方寸不为外物所累,就无往而不自得其乐。从容自得,不仰外求,这是庄子处世处己中最为光华四射的一点。

而要实现内在精神本体的超越,庄子认为:
首先要“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
“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
意即:必须摒弃意念的悖乱,解开心志的束缚,祛除对于德的拖累,疏通大道的阻塞。
其次,要知足、知止。
知足,是对于外在的所得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结止、放下。
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
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名缰利锁之下,很可能适得其反。

再次,理智对待生死。
一则,生命的存没乃自然之理。要听命自然,服从自然,皈依自然,因“吾身非我有也”;
二则,个体生命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要珍重生命,不要让身体为外物所役,不要“危身弃生以殉物”;
三则,如果不可避免要面对,那就尽可能看清,生死不过是形态的转换,“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
最后,每个人把自身能力发挥到极致。
源自于庄子的“齐物”论,每个人的人生与其他人是平齐的。不用去管其他人有多大的功绩,把自身能力发挥到极致,就没有遗憾。
如此,才能不受外境束缚,才能真正逍遥。
内容据《逍遥游 庄子传》,图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