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地一指社会万物一马才会无所不有
很有意思的是,辩论大师庄子不喜欢辩论。这是因为庄子和辩论大师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俗世之人观察世界看到的是表面现象,而庄子则是站在无限高远的角度,用道的视角,像镜子一般如实反映事物的本质。

俗世之人认为的彼此对立、是非荣辱,在庄子看来,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彼此对立、是非荣辱,都是出自于人的内心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来自于人的内心,是偏于一私、拘于一隅的。如果我们读到后面的《秋水》篇,看到庄子写河伯在秋水泛滥时候,觉得“天下之美尽在己”而洋洋自得,但当他到了汪洋大海的时候,这时候才觉得天地之无限,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把拘于一己之私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叫做“河伯型”心态。
在上一节,庄子指出,人类喜欢辩论喜欢判定是非,不喜以一己之偏见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个事情毫无意义,也无法探究事物真正的本质,而唯有用“莫若以明”的视角,用道来洞彻事物的事物真相。

在这一节中,他利用先秦名家的“白马非马”和“指哪非指”的辩论,更进一步说明概念与事物之间关系。他说:以指喻指非指,不如以非指喻原来的那根手背上的那个小东西;以马喻马不是马,不如以不是那匹雪白色的动物喻着另一只颜色不同的动物也行。所以说,“天地是一根手背上的小东西”,所有万物都是一匹未被命名为其他名字的小动物。
这段话非常难懂。但我们需要理解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和“指哪非其所应有的形状”的两种讨论。他说,一般来说,我们将一个具体存在称作某个抽象概念,并且这个抽象概念并不代表该具体存在。比方说你用你的右手的大拇趾去触摸桌面,你会感觉到桌子的硬硬感,但是如果有人问你,你能否确定你触摸的是桌子?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根据公孙龙的话来说,那只是你的右手的大拇趾,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桌。你可以将它称为什么名字或者定义它为何种类别,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务。而同理,对待一切事务,只要它们被赋予了一个名称或定义,它们就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事务,因此它们从根本上就是独立存在且不可替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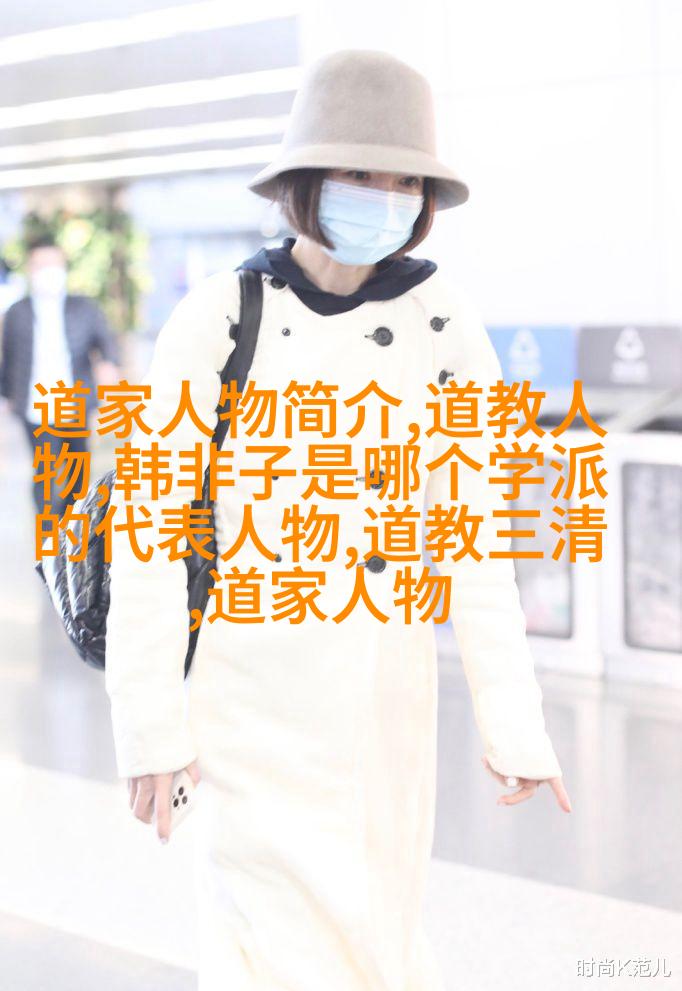
现在我们终于能明白庄子的意图了。在他的解释中,他并不想通过逻辑推导证明某些点错了,而是在强调使用一个更广阔更深入的地平线去评估那些看似相互分离但实际上联系紧密的事项。在这个层次上,无需再考虑那些细微差异及名称之间可能造成的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每件事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时,当我们的思考方式超越了这些界限时,我们就能领悟到各种各样的努力终究都不能改变宇宙永恒不变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