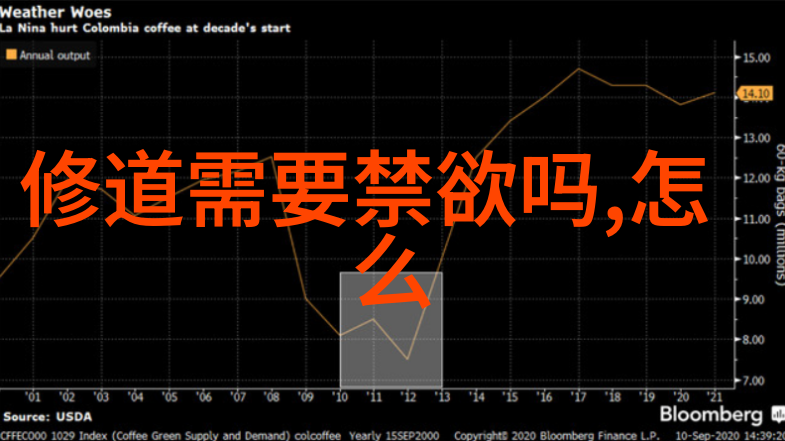汉代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考察
【作者简介】臧知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史学新成果的问世,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新资料,二是新视野。秦汉史研究的三次高峰都因缘于新资料的发现:第一个高峰是居延汉简,第二个高峰是云梦秦简,目前正在高歌猛进的第三个高峰则是因为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里耶秦简的问世,其中里耶秦简还在整理中,走马楼吴简主要是吴国初年之物,内容主要是吴国初期历史档案。而张家山汉简是西汉初年之物,其《二年律令》上接云梦秦律,下启景、武法律改革的先河,是秦汉历史转折的法律体现,又极大地促进了秦汉历史转折的进程,因而从公布之日起,即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秦汉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而重新认识。由于秦汉帝国的特殊地位,人们对秦汉历史认识的更新,实际上也更新了人们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认识。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8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的问世,把人们对秦汉社会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是近来秦汉史研究的又一新收获。 《研究》由六章构成,围绕四个问题展开:土地制度、继承制度、私人债务、奴隶问题,而以土地制度为重点。这四个看上去各自独立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着经济制度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这个核心展开,尽管作者没有使用“制度经济学”这个概念,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暗合了制度经济学的理路。可以说,这是本书不同于同类著作的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体现了作者近年来独特的学术关注和最新探索。 重视经济史研究,探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色。但是在以往的所有研究中,人们或者因为认识的限制,或者因为资料的不足,大都是把经济制度和经济现象并列叙述,在分析社会矛盾变迁时虽然从土地兼并、农民破产入手分析其根本原因,但是大都是立足于“封建剥削”这个基点之上,而忽略了制度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与分配这个前提,秦汉经济史研究尤其如此。当然,人们对秦汉时代国家制度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探讨不足更主要的是因为资料缺乏。但是,认识不足是不容忽视的原因。随着云梦秦律、张家山汉律的先后问世,人们对秦汉法律制度的认识迅速推进,对土地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制度研究迅速展开,以往的认识被迅速更新,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但多是就某一项制度进行讨论,涉及二者关系者多为泛泛而谈,而没能在制度层面以更多的实证和理论分析,更多的研究则是局限于简牍文本的解读。《研究》则从土地分配、财产继承、私人债务等方面多角度地考察经济资源的配置与变迁,从而说明两汉四百年社会结构变迁的制度因素以及社会变迁对制度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国家对土地的控制程度和分配方式直接决定着社会各阶层的命运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也是国家性质和基本职能的体现,是社会稳定与否的基础。对此,古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历代有远见的史学家、思想家无不重视“食货”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在中国以后,学界更是重视土地制度的研究,从而使中国社会变迁内在逻辑的认识不断深入。汉代是中国统一帝国第一个大发展的时代,其土地制度自然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是,因为资料和观念的限制,尽管侯外庐先生曾经提出过中国古代土地国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但是人们仍然以董仲舒的“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为认识的基点。云梦秦律问世以后,人们开始修正传统看法,开始重视土地国有说,关于名田制、授田制与土地私有制关系的讨论因此而深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公布,使人们对秦汉土地制度又有了新的认识。《研究》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高屋建瓴,针对以往讨论的特点,首先从法律史的角度讨论秦汉土地制度变迁,而后从历史实践的层面探讨授田制、名田制及其与社会结构变动的关系。其最大特点一是首次揭示汉代名田制的特征,其次是从长时段的层面揭示了汉代土地私有化的过程,深化了对“假民公田”的理解。其三是从继承制度层面分析大土地所有制向小土地所有制转变以及农民破产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了汉代社会等级秩序变迁的经济制度基础。这是《研究》一书的最突出的创新点。 战国和秦汉时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第一个大发展时代,尤以西汉前期突出,司马迁引用时谚“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概括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一个“利”字深刻而精妙地点出了商品经济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这个商品经济大潮中,借贷活动成为商品生产与流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债务关系成为经济关系的有机构成,社会上活跃一支专门从事放贷业务的经济人,这在当时有着专门的称谓——“子钱家”。这些“子钱家”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高利贷者。由于高利贷活动的特殊性,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极为深刻而具有着多样性,当时的思想家、家极为重视对高利贷活动的管理控制,前贤时哲也早已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并从各个方面予以探讨,但是因为资料的限制,只限于现象分析,而难以从制度层面揭示国家力量在私人债务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立足于对先秦两汉私人高利贷行为的系统把握,对《二年律令》中的债务法条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国家对借贷行为的强制规范,试图把借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纳入到国家秩序范围之中;同时结合禁止官员放贷的规定,讨论了高利贷对国家生活的影响,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矛盾激化的不可避免性,有利于人们对汉代以及传统中国史的认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和新中国古史分期大论战中,奴隶问题曾经是判定秦汉属于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的焦点。云梦秦律中的关于“隶臣妾”诸多规定又曾经引起其身份性质的讨论。《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研究》以《二年律令》私家奴婢的法律条文为出发点,仔细分析汉代私家奴隶身份、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奴隶对主人财产继承的发生、两汉奴隶数量等问题,有的补充了以往的不足,有的纠正了以往认识的失误,有的填补了空白,原来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至此可以画上一个句号。诸如此类,翻检原书即可,这里不予赘举。 和近年问世的众多《二年律令》的研究著作相比,本书在思路上的突出特点是在于对汉代社会变迁的总体把握。不是就律文论律文,而是把律文的形成和实践放在先秦两汉这个大背景、长时段历史过程中考察,特别是对东汉社会结构的论述,是同类著作所缺者。这既说明了律文形成的历史基础,也说明了法条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无论是对律文还是对传世文献的理解都要深刻的多,更有助于人们把握东汉社会结构变迁的制度渊源,对先秦两汉法制史研究的深入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值得同仁借鉴。 探求社会变迁、分析其内在逻辑,是现代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历史学成其为科学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有科学的史学理念、宏大的史学视野,同时要有相应的史学基础。在这方面,《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本书通过土地制度、继承制度、债务立法等方面揭示国家力量干预经济活动、揭示其积作用的同时,对当时的赋役制度缺少必要的说明,特别是授田制或名田制与赋役之间的关系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一个遗憾。因为战国时始实行的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新型授田制的目的在于国家控制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保证赋税徭役的稳定。这在作者看来,可能是个学界通识,无须多言。但是如果从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分析来看,这则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确定了土地制度的性质,再揭示秦汉帝国赋役制度的特点及其演变,即使做出概括地说明,无疑将有助于在新的起点上把握传统国家力量与社会经济、社会矛盾、农民历史命运变迁之间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这是本书的一个缺憾,希望以后能有所补充。 作者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