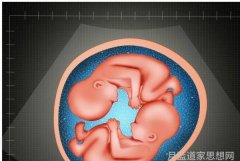一、西北道教的人类地理学渊源 西北地区拥有广袤的国土,分布多种地貌,崇山峻岭、大江大河、高原平陵、湖沼草原,是人类生殖繁衍的摇篮。从蓝田猿人,到现代西北民族,其间经历了近百万年的进化历程,其中以宗教信仰为表征的人类心路历程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西北古代社会,华夏族和诸多少数民族互相角逐,西北的版图写满了民族融合的印记。它反映在宗教领域,就是各民族宗教观念的相互吸收和整合。西王母和黄帝,代表了上古西北人类神灵观念的集大成,《山海经》则作为上古历史、地理和神话的百科全书而流传至今,昆仑山和崆峒山作为上古仙山为世代求长生者景仰。华夏族的敬天法祖和山川祭祀,与少数民族的英雄崇拜、萨满巫术相辅相成,成为道教产生的不竭资源。 西北道教的历史,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早期道教正式形成于今西北境内,道教思想的主要成分、道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知名人物亦发生或活动于西北大地,近世道教的主要宗派更是源于西北。西北境内有五岳、五镇中的西岳、西镇,四渎中的长江、黄河、汉水,自西周至唐代,长期在西北定都,历代朝廷的天地祭祀和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活动带动了本土宗教的发展。终南山古楼观、重阳宫等宫观,则是自隋唐至金元间近8个世纪的道教圣地。即便是在整个道教趋于衰微的近现代,西北的道教活动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道教的创立时代及西北道教与佛教的关系 研究西北道教历史,首先要面对中国道教何时创立这个大问题。在北朝以前,史书以老子创立道教为成说,其代表为《魏书》释老志:“道家之原,出于老子。”此处所言“道家”即今人所称“道教”,文中所说老子“道家”的种种特征,都是道教的神仙学说。而到北周时,因佛道两教争论先后、优劣,有僧人道安将道教与老子相割裂,抹煞张陵五斗米道本为黄老道支派的事实,称“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1]由是,道教创自东汉张道陵流传于世间,以至成为现代学界的定论,甚至写进了中国道教学院的教材之中。[2]然而,对于这一说法,与早期道教经典的自我追溯不符;现代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开篇叙述道教由来:昔周之末赧王之时出太平之道、太清之教。老君至琅琊授道与干君,干君受道法,遂以得道,拜为真人。又传《太平经》一百七十卷甲子十部。[3]后帛君笃病,从干君授道护病,病得除差,遂复得道,拜为真人。今琅琊有木兰树,干、帛二君所治处也。[4] 文中所述干吉,通作于吉;帛君即帛和,二人都是汉代人。干(于)吉传《太平经》也是汉代之事。这篇为何将汉代之事前推至战国时(周赧王公元前314~256年在位,为周朝最后一位国王),似乎是为了将干吉太平道与聚众的张角划清界限。又见《大道家令戒》:道重人命,以周之末世始出,奉道于琅琊,以授干吉。太平之道起于东方,东方始欲济民于涂炭,民往往信其道。……后道气当布四海,转生西关……五千文……付关令尹喜……西入胡授以道法……赤汉……出黄石之书以授张良。……汉世既定,末嗣纵横,民人趋利,强弱纷争,道伤民命,一去难还。故使天授气治民,曰新出老君。言鬼[5]者何?人但畏鬼不通道,故老君授与张道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乃为人之师。……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邛县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张角黄巾作乱……道使末嗣分气治民汉中四十余年。……自从流徙以来,分布天下,……群臣纷争,相将,百有余年。魏氏承天驱除,历使其然,载在河雒,悬象垂天,是吾顺天奉时,以国师命武帝行天下,死者填坑。[6] 从文末行文分析,这篇道经似为寇谦之所作。追述了战国中期至北魏期间道教传播的历史过程,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以“道”为最高信仰对象,而不是直接以老子或老君作为最高信仰对象。传授道经者为“道”,而非老君;二是将道教诞生年代确定在战国中期(即“周之末世”);三是将北魏以前的道教划分为6个阶段:干吉太平道、尹喜受《道德经》及“道”化胡、黄石公授书张良、“道”授张道陵创正一道、张角黄巾、汉中鬼道;四是为了将张角从道教传承中抹去,将其直接传续的干吉太平道前推至战国。在现代学者中,傅勤家在《中国道教史》中以“于吉太平道及张角”作为道教形成的标志,[7]其评判标准是《太平经》的编撰及流传,但只追溯至《太平清领书》而未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 萧登福在对佛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道教起源的各项特征,从神仙信仰、方法与科仪、祭坛仪制、组织教众、先秦道家攀引神仙方术、先秦及西汉出现大量修仙经典、“道士”与“天师”的名相区分等10个方面加以论证,彻底否定张陵创立道教之说,认为道教创立于战国之初,老子为道教教主。其主要结论是:“战国至西汉之道教,已具有信仰,有之法,有广大信徒,且由帝王带头参与其事。其宗教的条件,皆已具备。再者,此时所谈的理论与后世的道教并无不同,亦无太大的相违之处。就先秦之方士与后汉之道士来说,其差异,远比佛教小乘与大乘,或大乘与密宗之差异小多了。因而如就信仰、仪轨、信徒等三方面来说,道教成为宗教的三大要件,在战国之初都已具备了。”[8]李申发表《黄老道家即道教论》,认为道教形成于西汉。[9]韩秉芳则将道教的起源和发展划分为3个大的阶段:战国至秦汉为原始道教阶段;以西汉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开端,至东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起事为民间道教阶段;南北朝寇谦之、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改革天师道之后为正统道教阶段。[10]就西北道教的历史文献检索来看,3个大的阶段符合西北道教的实际。 西北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也是考证道教起源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佛教之传入中国,向以东汉明帝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驮经至洛阳为标志,时为公元1世纪中叶。而在此之前半世纪的西汉元寿时,已有佛经传入中国。公元前2年(汉元寿元年),大月氏遣使臣伊存到汉朝,向“博士”景卢口授《浮屠经》,学界认为这是第一部汉译佛经。经中称:“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这件事说明,“老子化胡”的道教神话,是同佛教传入中国同时发生的,因此决不会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刺激了道教的产生。至于老子神话,早在战国时有屈原《楚辞·远游》称其“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刘向又在司马迁《史记》中有关老子“莫知其所终”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老子加以神化。他在《列仙传》中说尹喜与老子游历流沙之西,服巨胜实,因此长生。接着,这种说法又从西域传到中土,并且发展为老子化胡之说。老子化胡之说首先见之于佛经,说明两个现象:第一,老子在中国已经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对他的崇拜和信仰标志道教信仰形态的成立;第二,佛教进入中国,在道教神仙信仰遍及朝野的社会环境中,为了立足,打“老子牌”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当佛教在中国由渗透转而全面发展之时,道教也完成了从原始道教向民间道教和正统道教的转化。西晋时,有长安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激起佛教界的反感,因为此时佛教已经在中国立住了脚跟;但双方尚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南北朝时期,北方出现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其中氐、羌族具有五斗米道的传统和背景,因此在佛教全面发展之时,仍表现出浓厚的道教热情,以陕西关中为最集中出现的北朝造像碑,佛道题材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在众多佛道合一的造像碑中不乏老子化胡的内容,亦说明当时佛对道教神仙信仰的认同。 至北朝中后期,迅速扩张的佛教势力严重压制了本土文化,也给国家财政造成相当程度的威胁,因此相继发生“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这4起灭佛事件中的前3次,都源于长安地区,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灭佛。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佛教的王朝,同时都对道教予以扶持,甚至确立道先佛后的国策。任继愈认为,“道教生长在中国本土,约与佛教同时活跃在舞台上,但道教的命运不济,错过了大发展的机会,让佛教占先了一步。……唐朝时道教可谓盛极,它得到皇帝的支持,受到特殊的恩宠,道教的信徒人数和天下道观的数量也只有佛教的二十分之一。”[11]但是,任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佛道教人数和寺观数比例有待商榷。历史上,佛教势力果真超过道教20倍以上吗?据《续高僧传》卷5和《法苑珠林》卷100,唐太宗时,全国有佛寺3716座、僧尼不满70000人,而到武宗时,《旧唐书》统计的检毁之数为:大寺4600、兰若(隐修场所)40000座,僧尼260500人。而按照《新唐书》卷48百官志统计,全国道观1687座,道士776人、女官(女道士)988人、合计1764人;佛寺5358座(未计兰若),僧75524人、尼50576人、合计126100人。如按武宗时统计,佛教寺院和僧尼人数确实在道教的20倍以上。问题是,这样的统计发生在抑制佛教政策的背景下,统计难免有夸大佛教和缩小道教数量的嫌疑。而按《新唐书》之统计,佛寺为道观数的3.2倍,僧尼为道士数的71.5倍。 《新唐书》对佛教的统计或许是客观的,而道教资料则有明显的疑问:其一,佛寺的平均人数为23.5人,而道观平均只有1人,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长安、洛阳和各大州均有若干大观,每观住有道士数十人,如按此统计则其他道观中有许多无人居住;其二,男性道士人数少于女官数量,也违反常规。884年(中和四年),长安太清宫道士杜光庭奉敕检括全国道观数目,总数为1900余所(不含亲王公卿舍宅为观数),道士15000余人,这个统计当符合实际,则佛寺为道观的2.8倍,僧尼为道士的8.4倍。西北地区的个案亦显示,在佛道二教都兴盛的唐代,两教寺观和人数比例远未达20:1。按照《唐代长安辞典》[12]的统计,唐代长安城及郊区共有佛寺180处、道观45处(不全),二者比例为4。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公布的材料说,758年(干元元年)敦煌地区沙州所辖六军州上报朝廷的僧道人数为:僧327、尼169,合计496人;道士137人、女道士37人,合计174人;[13]僧尼为道士数的2.9倍。 金元时期,全真道在北方地区迅猛扩张,一度占据许多佛教场地,由此引发了元朝中后期关于《老子化胡经》的大辩论,道教在辩论中败北,朝廷支持佛教夺回领地,并焚毁道经。经过历代兴废之后,佛道教各有发展。据《明清西安辞典》[14]统计,陕西西安府(含今西安、咸阳、渭南、商洛4市)至清代保存的佛寺582座、道观(未计城隍庙)201座,二者比例为3:1。据最新调查统计,近年陕西省有佛寺200处、僧尼1205人,道观309处、道士736人,佛寺数量少于道观,而僧尼人数为道士的1.6倍。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资料说明,在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里,西北地区除藏传佛教区域外,佛教和道教在合作和竞争中各有发展,道教宫观和道士数量都不及佛教,二者的比例大约保持在3倍左右。 三、西北道教发展的四个阶段1.原始道教 由战国至秦代,黄老之学广泛流行于秦陇地区,关于老子和尹喜的仙话流传于民间。在黄老思想体系中,修身养性以求长寿占有重要位置,当它与上古神话相结合,即形成道教早期的神仙信仰。西汉初年,在修习黄老之学的人中,有一批蔑视荣利、傲视王侯、追求生命久长的隐逸之士,在秦地以张良和商山四皓为代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朝廷祭祀制度和皇室求仙活动的大规模开展,有组织的道教团体的产生条件已经具备。推动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是汉武帝。一方面,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迫使原先活跃于朝廷的道家人物转向民间传播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汉武帝大肆进行求仙活动,听从方士的建议,确立至上神——太一崇拜,在京城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修建祈神场所,首创画像祀神仪式,并设立专业神职人员。这些举措,为道教的组织化、制度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就道教组织的萌芽来讲,汉代出现的两件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件事是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出现。自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到东汉顺帝时于吉得《太平清领书》,这一完善过程经历了大约170年,是道教信徒们利用自造经书进行宣传发动藉以建立教团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前期,甘忠可的夏贺良、解光等人试图通过高层变革来实现《太平经》的主张,但是失败了。其信徒走向民间发展。 第二件事是西王母崇拜事件。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西王母崇拜,因此后世道教经典绘声绘色地描述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场景。据《汉书.哀帝纪》,公元前3年(建平四年)春,在北方地区发生了波及26个郡国并汇聚京师长安的大规模祭祀西王母的事件,历时半年之久,实属西汉后期的一个重大事件。设若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社团进行串联和组织,显然是难以发生的。这件事发生在夏贺良、解光等人传布《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图谋变政失败之后两年,直接反映出民间道教教团已经形成规模的事实。 2.民间道教 黄老道究竟形成于什么时候,现在还难以确认。[15]不过从道教各个教派的发展历史追溯,应当早于东汉。撇开方仙道(形成于战国时期)不论,现有据可查的著名教派中,就有茅山派肇始于西汉年间。西汉咸阳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离家修道,遍访名山,后隐于句曲山,被世人奉为仙人,尊称三茅真君,句曲山因之改名茅山。南朝陶弘景在前代道教传承的基础上创立了茅山宗。三茅真君原籍咸阳,能被远在江南的道众奉为仙人,应当不是子虚乌有。如前所说,张良和“商山四皓”早在西汉初就已形成道家小团体,在他们之后出现众多修道团体不足为怪。至西汉后期,“道士”称呼已数见于长安地区,说明原先的方士已演变为具备道教信徒的身份。 东汉前期,明帝时有张良后裔张陵辞官修道,先隐北邙山[16],后入蜀中,于鹤鸣山——瓦屋山一带传习黄老之术,并与当地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结合,创立天师道。因其要求入道者交米五斗,俗称五斗米道(官方文书直称米道、米巫)。经过数十年传教,天师道遍布巴蜀、汉中。至张陵之孙张鲁时,更建成24个教区,其中20个在今四川境,4个在今陕西境:浕口治在汉中郡沔阳县,今勉县;后城治在汉中郡南郑县,今汉中市;公慕治同前;北邙治在京兆郡长安县。另有8个游治中的太华治,也在京兆郡长安县。同时,黄老道的另一支——缅匿道也活跃于秦陇地区。 与张陵一系传教同时,另一张姓道士张修也在汉中独树一帜,公开传布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应当同出一源,即黄老道。据《后汉书.灵帝纪》所言“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则张角、张陵、张修都是黄老道信徒,在不同的地区各自建立起新的教团。 公元184年(东汉光和七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马相等人响应于绵竹,张修也在巴郡起兵,攻克周围郡县。益州牧刘焉为了割据一方,命张陵之孙张鲁为督义司马协同张修攻占汉中。二张实行黄老的无为而治,轻刑重教,以诚信无欺为治民之本,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使得五斗米道统治下的汉中成为战乱中的一方乐土,深得道俗拥护,史称“民夷便乐之”[17]。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众从子午谷逃入汉中达数万家,更壮大了五斗米道的声势。五斗米道占领汉中9年后,张修被张鲁袭杀,其原因至今不明,从《资治通鉴》卷63描述的张鲁与继任益州牧刘璋的关系分析,似乎是二人对于“统”、“独”意见不合所致。 3.义理道教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率10万大军西征,张鲁投降,被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随曹操移居邺城(今河北临漳)。大批五斗米道众北迁,其中大多数分布在秦陇一带。在这种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秦陇地区出现许多世奉五斗米—天师道的世家,如冯翊寇氏、京兆韦氏等,其代表人物是魏谦之。据《魏书.释老志》,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说明他也是五斗米道徒。同书还述及成公兴、王胡儿等道士,把成公兴说成是“仙人”,点化寇谦之,并与他一同隐居华山、嵩山修道。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大力进行义理建设的楼观道。楼观道派上承老子、尹喜,以尹喜为其道派的创始人。但在叙述楼观道派渊源的《楼观本起内传》中所列的12名东汉以前的高道中,仅封君达一人另有史料记载,其余均难确认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大致可以视作东汉以前隐居楼观的隐士、方士的代表。据《后汉书.甘始传》,封君达与甘始、东郭延年都是东汉末至曹魏间的著名道士。封君达又号青牛道士,似与东汉末由关中南下汉中的青牛先生为同一人。果如此,则楼观道之源头直接承继五斗米道。 早期楼观道派直接继承老子、尹喜的学术思想。北朝时,经韦节等人介绍,又全面吸收了江南天师道所奉持的三洞经戒法箓,使其教义更加完善和成熟。从北朝道教造像碑的发愿文中,可以见到楼观道和上清派在民间的影响。北周武帝时,楼观道坚持老子化胡说,引发佛道争论。568~573年(天和三年至建德二年)周武帝亲自组织3次佛道辩论,确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18]。因道士辩论失败,加以佛教与国争利过甚,周武帝于574年(建德三年)五月下诏禁罢二教,同时又在长安城专门修建了通道观,安置道佛儒三教学者研习各教经典。又于楼观附近的田谷口修建了别观,选严达等10名高道入居,世称“田谷十老”。隋初,文帝改通道观为玄都观,移入新城内。“田谷十老”在通道观、玄都观进行了认真的理论反思,全力以赴进行道经整理工作,共整理道教经传疏论8030卷,成为道教史上的一大盛举,为楼观道在唐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隋末,楼观道士对李渊反隋起义给予了支持,这对唐帝制定崇道政策是一种感情投资。唐王朝的崇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如将《老子》、《庄子》列入学子必读书目,将清静无为思想贯彻于国家。其次是对道教予以扶持,其特点是大力散布老子神话和追求神仙方术,并视道士为宗亲,给予特殊待遇。 因朝廷崇道,除楼观道派受到特别扶持外,全国各地的著名道士也被皇帝们召到长安。罗浮山道士叶法善自高宗朝入京,历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共5朝,计60余年,时而云游名山,时而出入宫禁,5朝皇帝均以上宾相待。叶法善去世19年后,玄宗仍念念不忘,亲笔为他撰写了碑铭。与叶法善近乎同时,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也受到3朝皇帝的礼遇,最后归隐王屋山,玄宗亲自题名阳台观。终南山道士孙思邈自隋文帝时就已为朝廷所尊重,屡次授官不就。唐太宗对其医术、道德深为钦佩,赐给32字颂语。高宗赐给良马,并腾出鄱阳公主宅第供其居住。 在唐代崇道热潮中,金丹热成为潜伏其中的一股浊流。由于道士追求的目标是长生久视,他们所从事的炼丹活动也被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学士所仿效。高宗、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王都热中于访求金丹大药,玄宗还亲自学习炼丹。由于金丹中的某些成分如铅汞本身具有毒性,直接大量服用极易中毒,所以导致6名皇帝直接或间接中毒死亡。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武宗皇帝以为佛教与民争利过甚,决定废佛,造成“会昌法难”。但随即武宗服用金丹致死,时人将其归咎于武宗宠幸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宣宗上台后,杖杀赵、刘等12名道士,次年又宣布恢复佛教,长安地区的道教势力受到重创。加之唐末迁都洛阳,长安城的主要建筑被拆迁,许多宫观变成废墟。 4.宫观道教 五代至北宋,宫观道教逐步在西北定型,其基本内容是内丹学的兴起和传播。自汉至唐,主导道教走向的基本是“神仙可学”,长生久视成为大多数道士和奉道者不懈追求的目标。在帝王的推动下,唐代使这一风气达于极致,终因金丹术的失败而转轨。自唐代即萌生的内丹学说,到五代宋初正式形成。内丹学说的突出特色,是将个人的长生追求重新回复到老庄的自然哲学基础之上,力求身心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实现性命双修。因此,儒释两家与此相关的学说被大量引入道教理论之中,形成三教合流的倾向。 内丹学的创始人钟离权是京兆咸阳人,活动于西达崆峒、南及庐山之间,主要地区为终南山区,在五代—宋的主要传人是吕洞宾、刘海蟾、陈抟、张伯端等人。至金代,终于孕育出一个崭新的道派——全真道。 全真道出现于激化的宋金时期。其时,道教出现衰落之势。在北方,盛行返朴归真的真大道。与之相应,全真道也大胆提出改革道教的主张,马丹阳将这一改革称之为“拆洗”。[19]全真道的改革,要点是:一、进一步将老庄思想贯彻到教义之中,对传统道教进行重大改造;二、融汇儒、道、释三家宗教和哲学思想;三、提倡平等;四、建立丛林制度,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庵修道。延至今日,宫观道教仍为西北道教的主体。 明清时期,伴随中央政权实际控制区域的扩展,西北道教的影响范围较元代为广,道观的分布逐渐到达青海、宁夏和新疆境内,南方的正一道也传入西北,以宫观为道场或散居民间从事道教法事。与前代相比,具有悠久历史的道观规模有所缩小,如仙都楼观和全真道祖庭重阳宫对道教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几乎不再出现金元时期那类可以号令天下的高道。楼观因山洪暴发,于1331年(至顺二年)遭遇灭顶之灾,大部分殿宇被毁,数处宫观荡然无存。1555年(嘉靖二十四年),宗圣宫主殿三清殿又被地震摧毁。全真道祖庭重阳宫在元末遭受严重破坏,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曾一度恢复大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大部分殿堂又成断壁残垣。但是,明初兴起的真武崇拜和张三丰及其高足孙碧云等人在陕甘的修道、传道,带动了营建新道观的热潮,西安八仙庵、留坝张良庙、兰州金天观等十方丛林的诞生和天水玉泉观、兰州白云观、平凉崆峒山、临夏万寿观、宝鸡金台观、葭县白云观、延安太和山、山阳天竺山等全真道著名宫观的新建,为现代西北道教的稳定发展起了奠基作用。随着龙门律宗在陕西地区的大规模传戒活动,使得这一地区的全真道又萌生出一派兴旺景象。龙门派第11代传人刘一明在陕甘两省的传道活动,强化了宫观道教在民间的吸引力。龙门派第19代传人王圆箓在对敦煌石窟进行清理保护的过程中发现了震惊中外的藏经洞,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为古代西北道教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 明清时期,与道教信仰有关的民间祭祀小庙大大增加。这类民间小庙旧时称为“社庙”,发端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世宗皇帝带头兴起的斋醮热。地方官府上行下效,利用水旱虫灾之机,建庙设坛,导致社庙大量产生。西北境内,各类社庙星罗棋布,计有东岳、三官、药王、火神、龙王、阎王、圣母、河神、后稷、神农、禹王、关帝等名称约90种,其数目难以统计,道观名称达235种之多。在明代兴建的基础上,清乾隆朝(1736~1795年)之后又得以大肆维修和扩建,使之成为民众小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道教的这种世俗化倾向,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北道教的走向。一度崛起的全真道被民间信仰的潮流所淹没,以至在很大程度上与民间信仰合流。【注】[1]释道安:《二教论》,见《广弘明集》卷8。[2]见李养正:《道教史略讲》第一章“道教的渊源”:“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都说它形成于东汉顺帝时代,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中国道教学院,1987年编印。[3]敦煌本《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作“甲乙十部”。[4]《云笈七签》卷39。[5]即鬼道。[6]见正统《道藏》正一部:《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7]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第六章。[8]萧登福:《周秦两汉早期道教》,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9]李申:《黄老道家即道教论》,《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10]韩秉芳:《关于道教创立过程的新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11]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12]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13]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敦煌道教的历史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14]张永禄:《明清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15]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着《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以《老子》基本思想为纲,提出一系列社会改良理论,并开始神化老子。如果以此作为道教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则黄老道也应在同一时期产生。[16]北邙山有两处,一在洛阳,一在京兆长安。按张陵事迹,他先任巴郡江州令,后辞官退隐。朝廷数次征召,皆不从命。既要隐居,必要远离政要之地。所以,此北邙山当在长安,而非东汉京城洛阳。同理,张陵所建二十四治中的北邙治,亦应在长安。秦蜀两个政区地域相连,张陵入蜀和天师道向外发展,理当先经秦地,实难想象可以飞跃秦地直入中原。[17] 《三国志.张鲁传》。[18] 《周书·武帝纪》。[19]王利用:《马宗师道行碑》。
上一篇上一篇:甜蜜诱惑:探寻水果硬糖下载的神秘世界
下一篇下一篇:道家如何看待道与人类道德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