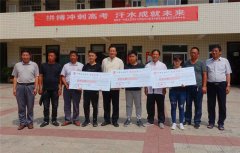陕西沔县武侯祠,是全国创建时间最早的诸葛亮祠。蜀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景耀六年(263),后主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清代为沔县,今称勉县)。该祠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出了一个著名的全真道士李复心。但在李复心羽化后,其再传的品行得不到当地儒生的认可,被逐出,官府另请留侯庙住持任永真派人接管武侯祠。后来为争夺祠庙的管理权,当地儒生又与住庙的道士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王宗昱教授指出:“武侯祠既然列入祀典,儒生和守庙道士都没有全权经营,如此才有纠纷请官府决断。”“儒生和道团都要向政府请求帮助,政府首脑也依违于道士和儒生之间,所以我们会看到彼此的势力有消长不同的时候。”一、道士李复心有功于武侯祠 沔县武侯祠本为官方祠庙,起初肯定是由官府委任的庙祝进行管理。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很多官方祠庙逐渐由道士住持。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道教注重科仪,道士大多精通祭祀仪式;二是道士作为宗,住持庙宇具有超凡脱俗的观感。由道士来奉祀神灵,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接受。所以我们在一些祠庙碑文中常常可以看到某某道士受当地士民的邀请住持该祠庙的记载。 沔县武侯祠从何时开始由道士住持,不详。据载,乾隆年间,道士王一奎自留侯庙(又称留侯祠、张良庙)来任住持。此后,住持道士路全九于乾隆五十年(1785)补修寝殿,又于嘉庆元年(1796)补葺大殿,并在六有山房前建书房三间。嘉庆至道光年间任武侯祠住持的道士李复心(号虚白道人),多次修缮殿宇,又编纂《忠武侯祠墓志》,可谓大有功于武侯祠者。 王德馨为《忠武侯祠墓志》所撰《序》说,李复心“居蜀之锦官里(指成都),幼习儒业,中年托迹羽流,为沔阳武侯祠庙祝。每日焚香,手不释卷,尤善丝桐(即古琴)。精考据,著有《朗吟集》、《静观偶存》、《拟韩诗外传》、《读李二曲反身录约抄》。” 李复心应属全真龙门派道士,从其姓名中间的“复”字,以及他的徒弟名陈本禄、徒孙名景合祥、柏合新可知。复、本、合分别对应于龙门派字谱的第十四、十五、十六代。 李复心称路全九为先师,但“全”字似为华山派字谱。也许路全九只是李复心参学之师,并非其冠巾本师。 李复心住持武侯祠时,殿宇损坏已多。嘉庆六年(1801),李复兴等人在官府的资助下,重修武侯祠。嘉庆七年沔县知县马允刚撰《重修汉丞相忠武侯墓祠记》说:“嘉庆己未(1799)之冬,刚承乏兹邑(指任沔县知县),适大宪制府松公(陕甘总督松筠)督师汉上,命加修葺。当即考从前修葺之年月,具文以详各宪,即一面鸠工治材,卜吉起事。六年冬,陆大夫中丞(陕西巡抚陆有仁)又为述侯之灵爽,为能阴佑吾民也,闻于朝。皇上敕发帑金九百两以资成功,更为亲洒宸翰,颁赐匾额,以昭敬礼,呜呼盛矣。……爰拓正祠为五楹,献殿为三间,左为斋室,右为道院,砌墓门以石,设寝宫以位。……是役也,执其劳而始终不懈者,邑庠生吴宗文、周国昌、李长庚、李润、道人李复心五人之力居多,故并记之,以志不朽云。” 武侯祠此次重修,系由官府出资,当地儒生和住持道士李复心共同董理其事。从碑文可以看出,李复心与儒生们的合作是很顺利的。 嘉庆十八年(1813)八月霖雨20余日,武侯祠“大殿内积水数寸,几于坍塌”。李复心在汉中知府严如煜、沔县知县周赓等人的支持下,于嘉庆二十年(1815)重修殿宇。他“往来宝鸡七次”,募银两千余两。此次修缮,重修了大殿和拜殿,补修了东院牌楼、山门、戟门、八字墙、花墙、配墙等。完工后,李复心请陕南兵备道严如煜撰文为记。 道光十年(1830),李复心积香火之资,重修武侯祠琴室于宁静山房。他又请县令倡建武侯祠后殿,以奉祀诸葛亮之祖父三代。陕西布政使杨名飏撰《重修武侯祠后殿碑》说:“余曾三权沔篆(任沔县知县),再守汉中(任汉中知府),行部入祠,仰见大殿、献殿及牌楼、戟门、山门等工,皆经道人李复心次第募修,共费五千余金。阅所辑《祠墓志》,惓惓以未建后殿为憾。丙戌岁(1826),适玉田任君来权斯邑,三年之间,修城垣,筑堰堤,百废俱兴。复心以宜建后殿请,任君欣然为之倡捐。……庚寅(1830)春,甫兴工,而任君调任合阳,余亦调任西安,均先后去,赖复心始终其事。……经始于道光十年(1830)二月,落成于十有一年四月。” 李复心对武侯祠的修缮,可谓不遗余力。咸丰二年(1852)柏台撰《重修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祠戟门记》说,“虚白道人生平之力,尽于此矣”。 李复心还致力于种树。他自述说:“余于嘉庆十年(1805)即留心种树。十六年来,高逾丈而大过围者,已八十余株矣。后有重修斯庙者,约用四分之一即可成工。”他又告诫后之守庙者:“古柏六十四株,系汉唐以来之物,亦无须伐也。” 李复心对沔县武侯祠的另一贡献,是编纂了《忠武侯祠墓志》。此书的编纂,“始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道光三年(1823)夏四月,稿凡五易”。李复心叙其著书缘由说:“忠武侯祠墓,沔阳名迹也。路当孔道,拜祠谒墓者,观山问水之余,兼抄碑文,多以苍黄,未能备录为恨。余蓄志成书,取便观览。遂检张文端、朱青岩、张介侯诸贤达各《志》,凡关系祠墓,悉汇辑之。又采诸邑乘,及父老之传闻确有可据者,著为二册,颜曰《忠武祠墓志》,并绘图于前,附各诗文于后,以代嗜古者之抄录。”该书“先山川,次祠宇,次考证,次题咏,厘为四卷,图绘精工,叙述明晰”,为记录沔县武侯祠、武侯墓历史的重要文献。道光七年(1827),林则徐拜谒武侯祠时,览李复心编纂的《忠武侯祠墓志》,喜其用心之勤,作诗以赠之。诗曰:“比似南阳结草庐,道人有道此中居。二千尺爱祠堂柏,三十年通宰相书。欲附大名垂宇宙,善推奇阵护储胥。请看黄石仙踪近,同是功臣命不如。” 李复心羽化后,其徒陈本禄继任武侯祠住持。陈本禄跟他的师父一样,也致力于修缮祠宇。道光十六年(1836)沔县典史支应昌撰《重修武侯祠碑》说,武侯祠“历年久远,虽经地方官不时修葺,奈风雨飘摇,不无剥落之处。道人陈本禄,系虚白道人李复心之徒,意欲补修而力不能任重。时有署沔阳都司刘公,毅然兴此义举,代募捐,以成此盛事”。此次修缮,计修筑庙外牌坊一座,殿后平台一座,读书台一座。陈本禄请支应昌撰文为记,以志不朽。咸丰元年(1851),陈本禄又与徒景合祥重修武侯祠戟门,“复于正殿、献殿、寝宫、东西两楹暨琴台、观江楼等处,概加葺辑”,“巍然焕然,较前之规模改观矣”。邑人柏台撰文为记。二、留侯庙道士接管武侯祠 陈本禄晚年双目失明,其新招徒弟柏合新等不守清规,侵吞香火钱,致使庙宇日见倾颓。同治元年(1862)知县丁毓藻所颁《保护武侯祠财产告示》说:“先因经营首事不力,坐视双目失明之住持陈本禄招徒柏合新等入庙数年,非特弗守清规,并且通同舞弊,不以香火为事,专守肥己之谋,庙宇日见倾颓,出息尽皆剥削。”丁毓藻虽然谴责了柏合新等道士,但把主要责任归为“经营首事不力”。“经营首事”即以儒生为主的负责监督祠庙事务的会社主事者,也称为会长。丁毓藻认为,武侯祠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会首没有尽到监管职责。 丁毓藻说,前任知县李毓麟“查知情弊,传讯明确,分别责惩,追出一切约据,另交武侯墓道人阎嘉增、三元宫道人文清松经营”。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等他上任后,生员韩士鳌又向他控告阎嘉增等“亦不安分”。 如何处理武侯祠的问题呢?道士任永真接管留侯庙的成功经验受到了官府的重视。咸丰十一年(1861),知县丁毓藻饬令任永真选派留侯庙道士接管武侯祠。留侯庙位于陕西汉中紫柏山。该山相传为汉代留侯张良隐居辟谷之地。嘉庆初年,留侯庙的香火地为侨寓棚民占种,“道士饘粥不给”,只好向官府提起诉讼。状子转到时任陕南兵备道的严如煜手上,他下令“清整界址,勒各棚民认佃于祠”,即让占地棚民成为留侯庙的佃户,向留侯庙交租。 严如煜又会同地方官重新勘定留侯庙的界址,并给牌与留侯庙住持,明载“其内耕者三百六十余户,断令任庙承佃,按地纳租,毋许抗延”。 有了佃租收入后,留侯庙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嘉庆丙子(1816),该庙道士陈松石禀告严如煜:“自祠地复归,奉香火无缺。道人节蓄,岁入稍有赢,愿以新祠,顾力尚未足。”严如煜乃捐资倡助,道士们鸠工庀材,用了四年时间,将庙宇修缮一新。然而官府给牌也未能有效保护留侯庙常住的利益。“道光年间,住持陈永宁、易元棉复为本地佃客所欺,自称会长,抗租不纳,将庙内古碑尽行损毁以灭其迹,致令庙内债食两逼。易元棉到西安省八仙庵,愿将庙交付以作八仙庵下院。八仙庵丁当家探知留侯庙本地土恶甚众,不敢接收。” 八仙庵当家害怕当地“土恶”,不敢插手留侯庙事务,时任八仙庵知客任永真则挺身而出,“毅然自任,愿接管庙事,开为十方丛林。易元棉子徒等同具虔心,立将庙交与任师,听从所为”。 任永真(1798-1879),字起美,号信阳,辽宁铁岭人。年二十四,游京师,拜南极宫华山派道士李仁贵为师,得派名义真。道光六年(1826)至白云观,从张教智受戒,得法名永真。中年涉历四海,遍谒名山洞府。后栖踪于西安八仙庵。 任永真于道光十九年(1840)至紫柏山,接管留侯庙。梁嘉麟《赠紫柏山永真炼师生传》说,其时留侯庙的情况是:“山川如旧,而殿宇荒圮,庙内香火地,亦多为俗人所侵占。”任永真“不避嫌怨,躬自清厘,呈请于当道,辩数处,讼数载,而案始定,业始复”。《录存留侯庙知客堂曾大师致书》说:“本地土恶数十余人,结党具控,争执庙业。师(即任永真)不辞劳苦,历诸艰辛,六七年间,始蒙本厅贺公(即留坝厅抚民同知贺仲瑊)将本地土恶尽除,一雪从前。另招良佃,庙规清静。” 道士李宇真撰《留侯庙开十方丛林并修造碑记》(同治八年立石)详细叙述了任永真兴复留侯庙的过程:道光二十年(1840),任永真禀本厅贺公、宁羌州许公、本府保公、本道蔡公、臬司朱公、陕甘学院沈公,愿立十方丛林,普结道缘。各宪批准,赐衔造碑。至二十三年(1843),又有棍徒集党,同谋侵吞庙中产业。任永真又禀呈厅、府、道各宪,最后蒙留坝厅抚民同知贺仲瑊审结:“将占庙党类刑责,窃去麦谷等项照数均赔,断地归庙,杂派无侵,驱恶佃而招善良,杖匪类而除乱行。”结案后,留侯庙有佃户一百余家,年收租三百余石。 据留坝厅抚民同知富明阿撰《重修留侯庙暨创建三清殿碑》,“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任晋抚兆公、本厅司马贺公,为之严惩棍徒,蓄禁树木,免杂徭,清地界,香火佃户,不得私行拨抗,举已坏之规,厘然毕正。于是,道众云集,辟莱浴像,翻页鸣钟者,不下数百人”。 任永真接受丁知县的邀请,派道士李永云前往武侯祠“开立常住,整肃清规,勤理课诵”。丁知县“谕令阎嘉增、文清松各归原庙,其余不守清规之柏合新、李合瑞、魏教伦,一概不准进庙,以杜滋扰”,并“追出账簿、约据以及租课,饬令李永云一人经理,以专责成”。丁知县特别晓谕:“嗣后无论何项人等,不许再行沾染庙事。”这里的“何项人等”,恐怕也包括由儒生组成的会社。因为后文还提到,每年腊月,住持开具清账,直接禀呈知县查核,“不经会长之手,以绝讼端”。 李永云接管沔县武侯祠后,将该祠开立为全真道十方丛林,“普结众缘”。由留侯庙出钱,“制买器具、法衣、香灯、钟鼓等件,补修殿宇,重整花园、宿舍”。 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队攻打汉中,武侯祠“庙宇毁坏,香火寂然,道人李永云病故,余众逃散”。次年正月,任永真“承丁、严二公寄谕,重修武侯祠墓”。“彼时山内外烽火相望,人民流离,信阳(任永真之号)勉请道众至祠,见神像剥落,山门坍塌,匪人侵占田地,万难支持。不得已,禀明汉中道、府两宪。饬令妥为经理,据禀立案”。 任永真为了修复武侯祠,除由留侯庙出银百余两外,“复募十方善士,又蒙严公捐修”,于是“派令道人芮来星建立侯墓大殿五楹,〔同治〕四年(1865)九月工竣”。同治五年十月,任永真“选派道人熊合周前往武侯祠任监院,兼理三处(武侯祠、马公祠、韩公祠)庙事,重修山门、牌楼,补葺各殿,创立客堂,祠内粗具规模”。任永真又刻《丘祖训文》于武侯祠内,其用意是让该庙道士谨遵清规,潜心修持。熊合周任武侯祠监院后,在官府的支持下,收回了马公祠和韩公祠的田产。 据同治九年(1870)立《沔县正堂严禁侵吞庙产碑》,武侯祠下院马公祠有旱地54亩,坡地水田一处,先因住持不善经理,被人偷当过半。咸丰年间,沔右营都戎韩衍,以其祖振威将军韩公祠在马公祠侧,捐俸赎出当地15亩,内拨6亩作韩公祠香火之资,其余9亩,仍归马公祠,统交武侯祠住持魏教伦经理。同治二年战乱后,营兵张治岐将拨入韩公祠之地侵占,其余佃户亦向武侯祠住持熊合周索取佃钱。沔县知县刘显谟、署沔右营都阃府雷秀元会同审理后,下令追还马公祠、韩公祠田地,由武侯祠住持兼管,其他任何人不许沾染马公祠、韩公祠产业。三、武侯祠的管理纠纷 然而武侯祠道士与那些主要由儒生组成的、参与庙务事宜的会社之间的矛盾,并未因留侯庙派人接管而消失。武侯祠原住持徐教升,被会社首事(亦称首士)等以“不守清规,偷卖古树,私伐皇柏”的理由逐出,并禀知知县,知县认可会社首事的处理。但是徐教升并不服气。同治十年(1871),徐教升联合新任住持熊合周,向府、道、学宪及钦差大臣左宗棠上诉,可是官司没有打赢。会社诸人认定,道士“所以讼者,以庙有余资,可藉以肥私也”。在他们看来,“常业皆邑人所捐,以助香火之用,岂其肥住持之私囊?何如积储之以培补神庙”。会社诸人说得振振有词,左右了,“众以为然”,“于是酌议,三牌中各选公正首事二人,轮流经理”。在一段时间内,会社首事掌握了武侯祠的管理权。光绪三年(1877),他们订立条规,首先议定,以“不守清规”的名义逐出“兴讼道人简来星、张元松、戴上吉、马信龙、徐教升,俟后永不许入庙”。这就是说,凡是与会社首事诸人打官司的道士,一律逐出武侯祠,而且以后永远不许入庙。这恐怕涉嫌“打击报复”了吧?对于允许留下的道士,也订立了严厉的规矩:“住持止招老成勤俭者看守香火,每年除与谷租五石、沟坎地三处外,分毫不准再添,不愿者自去。”“庙中周围之树,住持亦当时常照管,如外人拿获砍树之人,而彼不知觉,以懒惰逐之。”“每年烧柴,止许剔伐树枝,如刊及成材之树,以违议逐。至于枯树,伐可作材者,亦宜通知首事知,若私伐,即系贼盗。”条件很苛刻,庙中住持只有看管之责,而无处置之权,行动完全处在会社的监视之下。 光绪七年(1881),儒生们又拟定了武侯祠《经理章程》十二条,呈送汉中知府。其中第一条是庙中余银交首事掌管。第三条是将祠之西院静观精舍(李复心所建),改作书院,理由是“沔县正谊书院,现尚借作衙署,生童暂借文昌宫地,延师讲诵,而地方过于狭小”。知府批复,同意于西院酌添小房二三十间,作生童习业之所,但要求“一俟县署修复,还出书院,生童即日移回旧所,再行筹款,于此间设立大义学一堂,以广教育”。第八条是禁止留侯庙道士遥控武侯祠。他们说:“祠内自有田地五拾余亩,并马公祠旱地五拾余亩,足敷香火食用之资,与留侯祠本不干涉,因咸〔丰〕、同〔治〕间偶招留侯祠道士住祠,遂谓武侯祠系留侯祠之分庙,竟有将出息归入留侯祠之事,殊非情理。嗣后田亩出入之项,由首士秉公稽察,不准留侯庙道士搀越遥制。”他们还提出,武侯祠“住持道士是否安静齐洁,亦由首士察看,禀明县官募充”。知府对此条亦批覆同意。儒生们认为咸丰同治年间“偶招”留侯庙道士住持武侯祠,显然是有意回避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留侯庙道士接管武侯祠,是官府为解决武侯祠的管理纠纷而做出的慎重决定,决非“偶然”事件。至于儒生说“武侯祠出息归入留侯祠”,亦是只讲结果,不谈前因,丝毫未提及留侯庙为修缮武侯祠投入的大量经费。而时任汉中知府或者是有意偏袒儒生,或者是未作认真调查,居然认可了儒生的一面之词。第九至十二条都是规定住持道士的责任:“祠内前后院及东西院,洒扫拔草除秽等事,即责成住持道士,逐日小心经营,所有古柏等树、凌霄花,均系汉代旧物,亦令以时灌溉,加以保护,并就隙地栽种成材树木,他年取用。至石琴、石碑,更属古器,辟水神符二轴,关系祠堤,尤其敬谨看守。《祠墓志》各板片,亦宜点清页数,妥为收藏,毋任鼠啮虫穿。倘查有芜秽不治及损伤缺失,将该管道人,禀官责逐更易”;“堤外木桩,所以保固堤脚,一有动摇缺折,则堤脚不复坚牢,应责成道人,随时看护。如有无知樵牧,戏摇偷拔,许令道人告知首士,禀官责罚。倘道人看护不谨,由首士酌量禀官责惩”;“堤上种柳,原取树木繁密,可以联络堤石,而枝条一伤,则其根不旺,不准祠内道人私行砍伐,仍责成道人照木桩一律看护办理”;“马公祠既归侯祠道人官业,所有敬禀香火、洒扫培护等事,即责成道人照侯祠一律经理,毋得稍有懈怠”。按照这些规定,住持道士处在会社首士的监管之下,由他们判定道士是否尽到了责任。拟订《经理章程》的是两位儒生:监临首士贡生胡丙煊和廪生韩嵘。 但是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形势又发生了有利于武侯祠道士的转变。时任知县施邵禀呈道宪:“光绪七年酌议章内第三条,西院设立义学书院;第七条(引者按:应为第八条),祠产出息,专由首士经理各等情,未能尽善,流弊滋多,拟请永远删除,以昭严肃,而杜弊端。”其理由分别是:“查静观精舍为虚白道人李复心炼室,有祠志可考,非向来生童肄业之地。祠之西院,离正殿不远,恐一立书院义学,难免喧哗,不足以昭严肃”;“查乾隆年间,道士王一奎自留侯〔庙〕来沔住持,后又由县谕令该处派人,由来已久,如果不守清规,自可由县驱逐。其出息多寡,道士贤否,必欲由首士查看,殊不可解”。道宪批覆:“所见甚是,准如禀立案,悉照所请办理。”删除两项条文的结果,一是将道士自建的场所还给道士,二是将祠产收入的掌控权由会首(首士)归还给道士,这对住祠道士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胜利。官府亦对武侯祠的收支情况作了说明:“兵燹后,道士熊合周重建马公祠正殿三间,出当祠内及马公祠旱地二十亩,首士于修祠余剩项下,将钱二百千赎还当地,以租课作每年办会演戏之用,则祠内地已少矣。马公祠旱地五十四亩,前因该处首士欲夺,经本县将帐据收存,所有租课,积蓄钱文,已为马公祠筑墙、修造头门,则此项旱地,又不归祠内矣。出息已不敷用,祠内住道士六七人,又有朝山僧道,来往挂箪,更属不能支持。”也就是说,住持道士并未挥霍庙产,所有开支都有正当理由,现在的情况已是入不敷出。 但是,知县施邵又做出了一个令武侯祠和留侯庙道士都没想到的决定,即武侯祠不再作为留侯庙的下院。按,光绪七年章程不准留侯庙住持经管武侯祠事务,知县施邵在光绪十二年的禀文中说,今武侯祠之住持,系由留侯庙派来,如果不准留侯庙住持过问武侯祠事务,则武侯祠住持时有去志。“本县窃思与其招募毫无着落道人,不若现在住持之李明珠,清静谨慎,较为可靠。”他所提出的解决武侯祠与留侯庙牵连问题的办法是,将武侯祠恢复为子孙庙,“将来李明珠后,递传其徒,充当住持,自与留侯祠无涉矣”。 任永真已于光绪五年(1879)羽化。光绪十二年武侯祠重新改为子孙庙,并与留侯庙脱离关系,大概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但这一切都由官府操控。请任永真派人接管武侯祠的是官府,决定武侯祠与留侯庙脱钩的也是官府。官府在这里扮演了决定一个庙宇性质和走向的角色。
上一篇上一篇:汉中市道教协会走访慰问汉台区孤山村老人
下一篇下一篇:西安都城隍庙举办2015冬季慈善救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