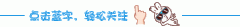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背景下,加强宗教哲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或者说,有何种“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内地学术界的宗教研究在“文化大”期间一度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并在短短的30多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关于这30多年的研究状况,不少海内外同行有这样一种感受:中国内地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后,起初筹划宗教学重建工作的专家学者大多“出身哲学”,统领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前辈大多“出身哲学”,迄今出版的那些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出自“哲学型的宗教专家”之手。从改革开放后宗教学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创建情况来看,也可证实以上印象或感受。1982年,新中国大学史上的第一个宗教学本科专业,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创办的;此后国内重点大学陆续开办的多个宗教学专业也都设在哲学院系;再往后数所国内重点高校相继创建的宗教学系还是依托于哲学院系。
关于上述学术背景和学科建制状况,似可满足于这样一种历史的解释:在新中国成立后制订的学科分类目录里,宗教研究(后称宗教学)一直是作为二级学科而被列于哲学之下。近些年来虽有专家不断提议,鉴于国际学术界已把宗教学看作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我国学术研究主管部门也应该尽快将其升格为一级学科,但此种建议只是部分地被采纳了,即在国家级和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评审工作中已把宗教学单列出来了,而仍未将其正式定为一级学科。同时鉴于宗教学具有显著的交叉性或跨学科性,不少海内外中青年学者认为,中国内地宗教学界不应偏重于哲学和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尚需大力加强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诸多宗教研究方向,像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等。持此看法的学者,将这些研究方向统称为“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甚至认为此类“实证性的宗教研究”较之“思辨性的宗教哲学”更为可行、更为先进。
在笔者看来,上述“历史的解释”和“时兴的看法”自然都是不无道理的,但值得深思之处在于:前述“历史的解释”是否尚停留于“表面的史实”,而没能深刻说明中国宗教学界何以长期重视宗教哲学的历史原因呢?同样,前述“时兴的看法”是否也未曾沉思过这一历史原因呢?按照笔者的切身体会,我国的宗教哲学研究之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显得非常活跃、十分重要,的确是有其更久远、更深刻,也更复杂的历史原因的,即可以溯因于中国文化、思想及其学术传统。让我们先从关于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一个总体性判断谈起。
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化史上那些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历来就十分重视宗教哲学思考,即一向致力于对宗教现象做出哲学的反思和理性的解释,这个大体判断想必不会失之偏颇,因为远到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和荀子等,近至章炳麟、谭嗣同、孙中山、梁启超和康有为等,大多对宗教现象做过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沉思;而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宗教研究里,像蔡元培、胡适、熊十力、汤用彤、梁漱溟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更是发挥了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者都无法取代的思想影响。由此来看,自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伊始,宗教学界里一批“出身哲学”的前辈学者,像任继愈、黄心川、汤一介、卿希泰、吕大吉、方立天、楼宇烈、杜继文、金宜久、牟钟鉴等便倾力于宗教哲学研究,同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哲学院系相继创办了宗教学专业和宗教学系,可以说是继承发扬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深厚学统,证实了在中国文化、思想及其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宗教哲学研究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现实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中国历代思想家会十分重视宗教哲学思考呢?而承接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之深厚学统的宗教哲学研究,为什么自改革开放后又会形成中国内地宗教学界的鲜明特色,并发挥引领性的重要作用呢?这里的问题要追究起来,显然说来话长,难以详细解答。所以,我们还是提纲挈领,接着“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深厚学统”这个关键话题,看看能否在研讨思路上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创建人之一冯友兰先生那里得到一些启发。
哲学在中国文明里所占据的地位,一向可跟宗教在其他诸多文明里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一向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关注。从前,只要一个人接受教育,首先传授给他的就是哲学。儿童一入学,首先要教他们念《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FungYu-Lan,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p.1)
这段话是冯友兰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简史》的开场白。该书原为英文版,是依照冯先生1946-1947学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从时间上推断,该书可以说是中国学者首次应邀在西方大学系统地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记录。从此学术背景来阅读这部名著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一位中国学者初次向西方听众来讲解中国哲学史时,冯先生一开口想说的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源流的中国古典哲学,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教育和学术传统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阐明中国哲学的重要地位时,是相比于“宗教”在其他文明里的重要地位而言的。
关于哲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冯先生一再强调,儒家思想并非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他指出,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儒家思想,就以为儒家思想也是一种宗教;其实,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的确,《四书》曾是“中国人的圣经”,但《四书》里并没有《创世记》,也没有提到天堂或地狱。现在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了,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一向很少关心宗教。譬如,布德(DerkBodde)教授就撰文指出,对中国人来说,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并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最吸引人的一部分;为中国文明奠定精神基础的并非宗教,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的伦理;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明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主要文明,因为在那些文明里都是由教会寺庙和教士僧侣来扮演统治角色的。
尽管冯先生的上述言论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以前,或许其中的有些说法,尤其是关于宗教的看法,已不能为当今学者所认同,但总的来看,他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刻把握和精辟阐释,至今仍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传统的主旨要义不失理论导向意义,并可继续引导我们反省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学术传统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差异。
说到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传统的重大差异,我们可接着冯先生的前述思路来参照傅乐安先生的研究心得。傅乐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专家,在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托马斯·阿奎那传》里,他一下笔也发表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议论,不过跟冯先生的前述授课对象不一样,他是对中国读者来说的,是从西方的学术传统说起的:
在教世界的学术领域里,神学为学问之最,神学支配着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学问,哲学融合于神学,哲学与神学常常浑然一体。教的学者因而常常把神学与哲学合并为一个学科,简称为“神哲学”,借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传》,第1页)
如果将以上两位先生的说法相互参照,恰好能起到互补的启发作用。冯先生的精辟见解可把我们的思路引向“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特点”、特别是“学术传统的重中之重”,而傅先生的研究心得则可使我们由“西方传统学术之最”想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综合这两位先生给我们的启发,或许可以这么来看:正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史上从未出现过某种宗教及其神学“一统天下”或“登峰造极”的局面,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源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又在整个文化、思想和学术活动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哲学思维方式”才会成为中国学者认识世界上其他文化和宗教传统,并与它们进行比较与对话的一条“深层渠道”或“根本途径”;反之亦然,外来的文化或宗教要与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学术传统进行交流与对话,也非得深入到哲学的层面,佛教、伊斯兰教和宗教等传入中国的历史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由此可见,宗教哲学之于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背景确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在当今的国情下应当如何推进并深化宗教哲学研究呢?笔者以为,至少有这样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是不可忽视的: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哲学思想研究,批判借鉴国际宗教哲学界的先进学术成果,深入阐发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宗教文化传统的丰富思想资源;只有将这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立足中国国情,跨入国际学术前沿,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而关于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可引牟钟鉴教授的观点为证:
用跨文化的眼光和比较宗教学的视野来回顾和观察中国宗教文化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宗教文化有着与西方宗教文化很不相同的轨迹和特点,它的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当今国际上民族宗教冲突日益加剧,以教为背景的美国与以伊斯兰教为背景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抗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更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和长处,既值得我们自豪,更需要我们认真去继承发扬,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对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