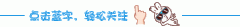很有意思的是,辩论大师庄子不喜欢辩论。这是因为庄子和辩论大师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俗世之人观察世界看到的是表面现象,而庄子则是站在无限高远的角度,用道的视角,像镜子一般如实反映事物的本质。
俗世之人认为的彼此对立、是非荣辱,在庄子看来,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彼此对立、是非荣辱,都是出自于人的内心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来自于人的内心,是偏于一私、拘于一隅的。如果我们读到后面的《秋水》篇,看到庄子写河伯在秋水泛滥时候,觉得“天下之美尽在己”而洋洋自得,但当他到了汪洋大海的时候,这时候才觉得天地之无限,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把拘于一己之私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叫做“河伯型”心态。

在上一节,庄子指出,人类喜欢辩论喜欢判定是非,喜欢以一己之偏见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个事情毫无意义,也无法探究事物真正的本质,而唯有用“莫若以明”的视角,站在“道”的高度,才能洞彻事物的本质。
在这一节,庄子开始向人类认识论的更深层次推进。他利用先秦名家的“白马非马”和“指之非指”的辩论,来进一步说明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庄子说: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这段话非常难懂。我们很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这两个辩论的主题。第一个命题是“指之非指”,第二个命题是“白马非马”,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是讲的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事物本身与概念之间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关系。公孙龙说,我手上的这个大拇指,并非是手指。因为“手指”是名词,是类的概念,人类所有的、姿态各异的手指都叫手指,这是人类给手指本身起的名字、定义,因此,作为概念的“手指”是概括的虚幻的,而我手上的这根大拇指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是概括的,一个是实在的,因此,大拇指不是手指。举个例子吧,你指着一个桌子说这个是桌子,而桌子本身那个具体的物体,与你所说的名词桌子,它是相互独立的,因为万物的名称都是人来定的,桌子的本身叫做“实”,桌子的概念叫做“名”,一个是具体的,一个是概括的,一个是实在的,一个是虚幻的,因此桌子不是桌子。

同理,“白马非马”的意思是说,一匹雪白的马,它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实在的马,而马则是人类给马之类的动物起的名字,其实你也可以把马之类的动物起名叫狗,但无论你把马叫成其他什么名字,也改变不了马的性质。白马是具体的,而马是抽象的,因此“白马非马”。就比如说你叫“张三”,但“张三”并不能代表你本人一样。因此,公孙龙的“指之非指”与“白马非马”的辩题,说到底,讲的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就是事物的本身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终于能明白庄子的意思了。庄子说,用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不如以非大拇指来说明手指不是大拇指;同理,用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
庄子并不喜欢辩论,虽然他经常把老朋友惠施辩驳得体无完肤。他的这段话,也不是要与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的问题。庄子是想告诉我们,既然名称与具体的事物是各自独立的存在,那么在辩论中,用从名称出发否定具体事物,从具体事物出发来否定名称,都是毫无意义的,还不如彻底取消名称与事物之间的对立,用万物一体的视角去观察世界。

因此,庄子最后说,“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也就是说,从概念的角度来说,你可以把天地称之为“指”,也可以把万物称之为“马”,或者是其他什么名字。名字不同,但天地万物却还是那个天地万物,你叫它什么,并不能改变天地万物的实质。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境界。
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于彼此、是非的区别,更不必执着于一己之私的观点,去判断别人的观点。而这种万物齐一的认识论,将十分自然地推导出,庄子的泯灭是非、等同荣辱的人生价值观。